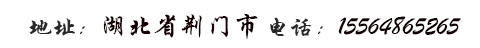宋代广州的国内外贸易
|
复方卡力孜然酊的价格是多少 http://baidianfeng.39.net/a_wh/140712/4424748.html 一、概说 (1)宋以前广州贸易的发展 中国历代的政治都市,由于社会经济的发展,地点往往变迁。在古代,商业都市差不多全在内地,如长安(长安所以成为都市,当然以政治的意义为重,但靠政治吃饭的人多半有钱,而秦、汉政策又常徙天下富豪于长安,故为满足这些购买力的大消费者而发展的商业也很有可观。《汉书》卷五九《张汤传》记有“长安富贾”,可以为证。所以长安同时也可说是商业都市)、洛阳、邯郸、阳翟、定陶、临淄、寿春、合肥、成都、郢等(见《史记·货殖列传》)都是。因为这时贸易的路线以河流为主(自然,货物也有陆运的,但陆路运费贵,体积大而价值小的货物往往因负担不起高昂的运费而不能贩往其他地方),所以上述的都市多沿着内地的河流旁边而发展,而所经营的多半为国内贸易。及中古时代,中国海运渐渐发达,沿海遂勃兴了好些都市,这尤以唐、宋时代为甚。如广州、泉州、福州、温州、明州、杭州、澉浦、华亭、江阴军、扬州、楚州、密州、登州及莱州等,都是在海边发展出来的都市,而且大部分又是在中古,尤以唐、宋时代,发展起来的。在这些沿海的商业都市中,发展最早,资格最老的,要算广州。所以在研究宋代广州的贸易以前,我们要把宋以前广州商业的发展情形考察一下。 广州贸易的起源甚早。据日人藤田丰八的意见,广州在秦代已经是犀角、象齿、翡翠、珠玑的集散市场。他所著的《宋代之市舶司与市舶条例》第一章云: 中国之海上贸易,单就记录上观察,则可远溯至古代。如《淮南子·人间训篇》所云,秦始皇之所以有南越之经略,是为得“越之犀角、象齿、翡翠、珠玑”之利,故发卒五十万为五军,以一军驻“番禺之都”。秦始皇之经略南越,其目的固然不像《淮南子》所说的那样细小,然南越之都会番禺,即广州,当时已为犀角、象齿、翡翠、珠玑集散之中心市场.似无疑义。(据商务出版之魏重庆译本) 到了汉代,广州也是珠玑、犀、瑇瑁等商品的集散地。《史记》卷一二九《货殖列传》云: 番禺,亦一都会也,珠玑、犀、瑇瑁、果、布之凑。 又《汉书》卷二八《地理志》云: 粤地……处近海,多犀、象、瑇瑁、珠玑、银、铜、果、布之凑。中国往商贾者,多取富焉。番禺,其一都会也。 除了上述各种商品以外,四川的枸酱也经由夜郎贩人广州。《汉书》卷六五《西南夷列传》云: 南粤食(唐)蒙蜀枸酱。蒙问所从来。曰,“道西北胖柯江。江广数里,出番禺城下”。蒙归至长安,问蜀贾人。独蜀出枸酱,多持窃出,市夜郎。夜郎者,临牂柯江。江广百余步,足以行船。南粤以财物役属夜郎,西至桐师。然亦不能臣使也。 又当时中原的铁器也贩往南越(见《史记》卷一一三《南越尉佗列传》及《前汉书》卷九五《南粤王赵佗传》),而广州那时又是南越最主要的都市,这些铁器当然以输入广州为多。 据夏德(Hirth)等的研究,在3世纪的时候,从事海上贸易的阿拉伯人已经在广州设有居留地: 在上古和中世纪的时候,一方面在埃及和波斯间,他方面在印度和辽东间的海洋贸易,似乎显然地握在南阿拉伯沿岸的阿拉伯人手里,在此时,他们沿着印度河口以南的海岸的重要港口,都设立堆栈,而以3世纪时在广州所开辟的居留地为其极点。(HirthandRockhill,ChauJuKua,序文) 按公元3世纪约略相当于魏、晋时代。在这时,据《晋书》的记载,有好些珍异的奢侈品由海外输入: 广州包带山海,珍异所出。一箧之宝,可资数世。(卷九○《吴隐之传》) 到了南朝,广州的海外贸易更为发达。《南史》卷五一《萧励传》云: 广州边海,旧饶外国舶至。多为刺史所侵,每年舶至不过三数。及励至,纤毫不犯,岁十余至。 又《梁书》卷三三《王僧孺传》云: 寻出为南海太守,郡常有高凉生口及海舶每岁数至,外国贾人以通货易。这时与广州通商的国家之见于记载者,有诃罗陁国: 西南夷诃罗陁国元嘉七年遣使奉表曰,“……伏愿圣王,远垂覆护,并市易往反,不为禁闭。……愿敕广州时遣舶还,不令所在有所陵夺。……”(《南齐书》卷五八《扶南传》) 及扶南国: 宋末,扶南王姓侨陈如,名阇耶跋摩,遣商货至广州。 永明二年,阇耶跋摩遣天竺道人释那伽仙上表称扶南国王臣侨陈如阖耶跋摩叩头启曰,……又曰,“臣前遣使赍杂物行广州贸易……”。(均见《南齐书》卷五八《扶南传》) 由于广州官吏的富有,我们可推知当时广州因经营海外贸易而得的财富之巨大。《南齐书》卷三二《王琨传》云: 南土沃实,在任者常致巨富。世云,“广州刺史但经城门一过,便得三千万也”。 及隋、唐时代,由于海上交通的发达,广州的贸易更有进一步的发展。《隋书》卷三一《地理志》云: 南海交趾,各一都会也。并所处近海,多犀、象、瑇瑁、珠玑奇异珍玮。故商贾至者,多取富焉。 这是隋代的情形。又《旧唐书》云: 南海郡利兼水陆,瓖宝山积。(卷九八《卢怀慎传》) 广州有海之利,货贝狎至。(卷一六三《胡证传》) 又《新唐书》卷一二六《卢奂传》云: 南海兼水陆都会,物产瓌怪。 这是唐代的情形。这时外国船舶及商人多往广州贸易。其热闹情形,据《唐大和尚东征传》所载,有如下述: (广州)江中有婆罗门、波斯、昆仑等船,不知其数。并载香药珍宝,积载如山。其舶深六七丈。师子国、大石国、骨唐国、白蛮、赤蛮等往来居住,种类极多。 其中尤以师子国的商船为最大。唐李肇《国史补》卷下云: 南海舶,外国船也。每岁至安南广州。师子国最大,梯而上下数丈,皆积宝货。至于在广州贸易的外国商人,数量也非常之大。黄巢作乱,曾在广州杀害外国商人及回教徒十二万至二十万之多。(见张星琅《中西交通史料汇篇》第三册第一三○页引AbuZaidHassan之纪录) 由上所述,可知广州在国内外贸易(尤其是国外贸易)上发展之早,历史之长。广州在中国历代对外(尤其对南洋各国)贸易上所以都占重要地位,据作者的意见,是由于它与腹地(Hinterland。一方面消费由海港输入的外国商品;他方面生产由海港输往外国的商品)的连络比较密切、便利的原故。在沿海各港中,广州与腹地(尤其当时政治中心)的连络,大半有便利的河流可供运输(以前运输以河流为主,因运输费贱而安全。至于海运,则尚未发达;陆路则难运,而运费又贵)。在广东方面,有北江可一直由广州至北境。其中走陆路的只是大庾岭一段。过岭后,江西又有水道人长江、运河,以至各生产地及消费地。所以由于唐代起对于大庾岭道的开凿[1],我们可得知当时广州与腹地关系密切的消息。反观其他海港,便没有这种与腹地连络的便利交通线。例如福建的泉州、福州,它们不特没有可航的河流与腹地(各省的生产地及消费地)连络,就是与本省内地的交通,也因河流(如闽江)之湍急,以及斜度太大,而感不便。故南宋以前,福泉等州在海外贸易上的地位,不如广州样重要。至于自南宋起,泉州所以日形重要,是因为当时政治中心南移杭州,与之较为接近,而当时除河流外,沿海岸线的运输也较前发达的原故。(2)宋代广州在对外贸易上的地位与广州政府对于海外贸易的奖励 以上是宋以前广州贸易发展的情况。到了宋代,由于上述的理由(有便利的交通线,以与腹地连络),广州在对外贸易上的地位尤为重要。在沿海各港中,以广州的对外贸易为最发达,大有压倒其他一切海港的趋势。这由于广州因海外贸易而得的税收,大于他港,可以推知。《宋会要.职官》四四云: (绍兴二年)六月二十一日,广南东路经略安抚提举市舶司言,“广州自祖宗以来,兴置市舶,收课入倍于他路……”。 (建炎)四年二月二十六日,尚书省言,“广南路提举市舶司言:检准敕节文,广南市舶司状:广州司舶库逐日收支宝货钱物浩瀚……” 又朱或《萍洲司谈》卷二云: 崇宁初,三路(广东、福建、两浙)各置提举市舶司。三方唯广最盛。 又清梁廷柟《粤海关志》卷三引毕仲衍《中书备对》所载神宗熙宁十年外国贸易的统计,而加以论断云: 谨按:《备对》所言三州市舶司(所收)乳香三十五万四千四百四十九斤,其内明州所收惟四千七百三十九斤,杭州所收惟六百三十七斤。而广州所收者则有三十四万八千六百七十三斤。是虽三处置司,实只广州最盛也。 由此可知广州在宋代对外贸易上所处地位的重要。 广州既然是宋代最大的贸易港,所以它的繁荣完全建筑在海外贸易上。沈括《长兴集》卷二五《张中允墓志铭》云: 其后用师于夏州,天下搔于兵,复议益赋于五岭。君时为广州四会尉,谓使者曰,“交(广?)州地非能饶也。大商贾胡赖以富者,其根乃在异国。知将困之,彼则踔海而去,昼夜万里,广遂将不为州矣。与其无事而失广州,孰若捐尺寸之利,为百姓计多也”。使者然其言,为格其令。 因为广州的繁荣与海外贸易有这样密切的关系,所以广州政府对于海外贸易非常奖励。上述政府在对西夏用兵时,军费大增,也不加税于广州,是奖励的一种表示。复次,广州政府对于从事海外贸易船只也给予种种便利。例如因为蕃舶常苦飓风,广州政府便开凿内壕,以便它们避风。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八三载大中祥符七年七月壬辰,广州言,“知州右太中大夫邵煜卒”。州城濒海,每蕃舶至岸,常苦飓风。煜凿内壕通舟,飓不能害。及被疾,吏民蕃贾集僧寺设会以祷之。其卒也,多陨泣者。(《宋史》卷四二六《邵晔传》有相同的记载,但“邵煜”作“邵晔”。) 再次,每年十月蕃舶归国的时候,广州政府照例设宴为之饯别,以示慰劳。这叫做“犒设”,也是奖励海外贸易的表示。其犒设的情况,桑原骘藏《蒲寿庚考》(陈裕菁译本)第二章已有叙述,故不再赘说。不过这里要注意的是:广州官吏招待这些海外贸易商人的礼意,厚于其他海港。《宋会要·职官》四四载: 绍兴十四年九月六日,提举福建路市舶楼踌言,“臣昨任广南市舶司,每年于十月内,依例支破官钱三百贯文,排办筵宴,系本司提举官同守臣犒设诸国蕃商等。今来福建市舶司,每年只量支钱委市舶监官备办宴设,委是礼意与广南不同。欲乞依广南市舶司体例,每年于遣发蕃舶之际,宴设诸国蕃商,以示朝廷招徕远人之意”。从之。 关于广州官吏之犒设,我们更应注意的是:不单从事海外贸易的主要人物(纲首)被邀参加,其附属人物如作头、梢工(即水手)等也被邀赴宴,以示对于海外贸易的奖励。同书《职官》四四载绍兴二年六月二十一日,广南东路经略安抚提举市舶司言,“广州自祖宗以来,兴置市舶,收课入倍于他路。每年发舶月分,支破官钱,管设津遣。其蕃汉纲首、作头、梢工等人,各令与坐,无不得其欢心。非特营办课利,盖欲招徕外夷,以致柔远之意……”(3)外商对于广州贸易的经营 宋代关于广州海外贸易的经营,以外国商人(尤其是大食,即阿拉伯商人)为重要主角。这由于下列一事,可以知道。《宋会要·职官》四四载绍兴七年闰十月三日,上(宋高宗)曰,“市舶之利最厚。若措置合宜,所得动以百万计。岂不胜取之于民?朕所以留意于此,庶几可以少宽民力尔”。先是诏令知广州连南夫条具市舶之弊。南夫奏至,其一项,“市舶司全藉蕃商来往货易。而大商蒲里亚者,既至广州,有右武大夫曾纳利其财,以妹嫁之。里亚因留不归”。上今委南夫劝诱里亚归国,往来干运蕃货,故圣谕及之。 政府因海外贸易的发达而得的税收很大,而经营海外贸易的重要主角是外商,所以政府要劝外商蒲里亚返国营运货物,不要因为舍不得离开他的中国太太而久留广州。而凡是姓蒲(Abou,Abu)的人,经桑原骘藏的考定,为阿拉伯人(见《蒲寿庚考》第三章)。由此可知,外商,尤其是阿拉伯商人,是宋代广州海外贸易的重要经营者。 关于宋代外商在广州的情形,如住居蕃坊(又名蕃巷),享有治外法权,信回教,不吃猪肉,其子弟人“番学”读书……等事,桑原骘藏在《蒲寿庚考》第二章中已详为考证,兹不赘述。这里要提出来说的,是桑原所未注意到的三数点。当时在广州的外国商人,除如上边所说,娶中国女子为妻外,又有带同妻子来广州居住的。《宋会要·刑法》二二载景祐二年十月九日,前广南东路转运使郑载言,“广州每年多有蕃客带妻儿过广州居住。……” 其次,在广州的外商,除有蕃坊(或蕃巷)居住外,又有“蕃市”,以便从事贸易。《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一二八载康定元年八月己酉,工部郎中天章阁待制知广州段少连为龙图阁直学士知泾州。广州多蛮徭,杂四方游手,喜乘乱为寇。会上元然灯,有报蕃市火者。少连方燕客,……作乐如故。须臾火息,民不丧一簪。众服其持重。 复次,因宋代在广州的外商甚多,外国的风俗也传人广州来了。斗鸡便是其中的一种。周去非《岭外代答》卷九云: 芥肩金距之技,见于传而未之睹也。余还自广西,道番禺,乃得见之。番禺酷好斗鸡,诸番人尤甚。鸡之产番禺者,特鸷劲善斗。其人饲养,亦甚有法。斗打之际,各有术数,注以黄金,观如堵墙也。……番人之斗鸡者,又乃甚焉。所谓芥肩金距,真用之。其芥肩也,末芥子掺于鸡之肩腋。两鸡半斗而倦,盘旋伺便,互刺头腋下,翻身相啄。以有芥子能眯敌鸡之目,故用以取胜。其金距也,薄刃如爪,凿柄子鸡距。奋击之始,一挥距,或至断头。盖金距取胜于其始,芥肩取胜于其终。季孙于此,能无怒耶! 读了这段文字,使我们不自禁地联想到现今欧美人士把跑马的风俗传人我国沿海各都会。 宋代广州海外贸易的利润非常之大。外商经营的结果,获利甚多,所以都非常富有。如番商辛押陀罗,家财多至数百万缗。苏辙《龙川略志》卷五云: 番商辛押陀罗者,居广州数十年矣。家资数百万缗。 其中尤以姓蒲(桑原骘藏《蒲寿庚考》第三章考定为阿拉伯人)的商人,更为富有。《东南纪闻》(撰人佚)卷三云: 番禺有海獠杂居。其最豪者蒲姓,本占城之贵人也。后留中国,以通来往之货。居城中,屋室侈靡,富盛甲一时。 又岳珂《桯史》卷一一云: 番禺有海獠杂居。其最豪者蒲姓,号“白番人”,本占城之贵人也。既浮海而遇涛,惮于复反,乃请于其主,愿留中国以通往来之货。主许焉。舶事实赖给。其家岁益久,定居城中,屋室稍侈靡踰禁。使者方务招徕,以阜国计,且以非吾国人,不之问。故其宏丽奇伟,益张而大,富盛甲一时。绍熙壬子,先君帅广,余年甫十岁,尝游焉。……他日郡以岁事劳宴之,迎导甚设,家人帷观。余亦见其挥金如粪土,舆阜无遗,珠玑香贝狼藉坐上,以示侈。帷人曰,“此其常也”。…… 由于广州外商的有钱,我们固然可推知他们从事海外贸易的利润之大,同时又可推知:因为他们富有,资本多,其贸易的规模一定很大。 宋代的外国商人,除经营广州的海外贸易外,同时又经营广州与国内其他都市间的贸易。他们将由海外输入广州的货物转贩往当时大消费中心的汴梁(汴梁是当时大消费中心的理由,见拙著《北宋汴梁的输出入贸易》)及其他地方出卖。《宋会要·职官》四四载崇宁三年五月二十八,诏,“应蕃国及土生蕃客,愿往他州及东京贩易物货者,仰经提举市舶司陈状。本司勘验诣实,给与公凭,前路照会经过官司常切觉察,不得夹带禁物及奸细之人。其余应有关防约束事件,令本路市舶司相度,申尚书省”。先是,广南路提举市舶司言,“自来海外诸国蕃客,将宝货渡海赴广州市易务抽解,与民间交易,听其往还,许其居止。今来大食诸国蕃客,乞往诸州及东京买卖,未有条约”。故有是诏。 又《宋史》卷一八六《食货志》亦载崇宁三年,令蕃商欲往他郡者,从舶司给券,毋杂禁物、奸人。初,广南舶司言,“海外蕃商至广州贸易,听其往还居止。而大食诸国商亦丐通入他州及京东(《会要》作‘东京’,‘京东’误;因为汴梁,即东京,是当时的大消费中心,在那里的购买者多而富有,故由海外输入广州的商品多转贩到汴梁,以便取得善价)贩易”。故有是诏。 又《宋会要·蕃夷》七说在广州的外商冒充进贡使臣的随员,以便人汴贸易云: (大中祥符九年)七月七日,秘书少监知广州陈世卿言,“海外蕃国贡方物至广州者,自今犀象珠贝拣香异宝,听赉持赴阙……每国使副判官各一人。其防援官大食、注辇、三佛齐、阖婆等国勿过二十人,占城、丹流眉、渤泥、古逻、摩迦等国勿过十人,并来往给券料。广州蕃客有冒代者罪之。缘赐与所得贸易市杂物,则免税算。……”从之。(4)华商对于广州贸易的经营 宋代广州的国内外贸易,如果全被外商包办,那就是被动的,不见得有利;如果他们不来经营,贸易便要衰落。可是事实上广州同时又有好些华商赴海外或内地贸易,因此广州的贸易是主动的,大部分利润仍在我国商人之手。 上引《宋会要·职官》四四说广州政府犒设从事海外贸易的商人时,“其蕃汉纲首、作头、梢工等人,各令与坐,无不得其欢心”。又《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九四亦载天禧三年九月乙卯,供备库使侍其旭言,“广州多蕃汉大商……”。 可知在宋代广州贸易的经营上,不单是外商,华商也占有同样重要的地位。 在宋代,航行于南洋一带的中国商船非常发达。关于此点,桑原骘藏在《蒲寿庚考》第二章已有详细的论证。兹引其结论如下: [华船发达之概观]总上所论,南洋贸易船,自法显后,代有进步,载量曰增,设备曰周,航术日精。降至宋元,益臻其极。自法显义净始,经六朝而至隋唐,往天竺之僧,概乘外船。七八百年后,奥道力克(Odoric)、伊本巴都他(IbnBatuta)、马哥孛罗(MarcoPolo)等外人,往来华印之间,多乘华船,其故可想也。 中国在南洋一带的商船既是这样发达,中国商人当然是经营海外贸易的重要主角了。 宋代广州市舶司常常发舶往南洋诸国贸易。《宋会要·职官》四四载崇宁五年三月四日,诏,“广州市舶司旧来发舶往南蕃诸国博易回,元丰三年旧条,只得却赴广州抽解……”。 这是北宋的情形。至于南宋,《宋史》卷一八六《食货志》载乾道三年,诏,“广南两浙市舶司所发舟还,因风水不便,船破樯坏者,即不得抽解”。 在这些由广州发往南洋各国的商船中,有许多华商前往贸易。这可以下面的故事为证。曾敏行《独醒杂志》卷一○云: 庐陵商人彭氏子,市于五羊,折阅不能归。偶知旧以舶舟浮海,邀彭与俱,彭适有数千钱,谩以市石蜜。发舟弥日,小憩岛屿,舟人冒骤暑,多酌水以饮。彭特发奁出蜜,遍授饮水者。忽有延旦丁十数,跃出海波间,引手若有求,彭漫以蜜覆其掌。皆欣然舐之,探怀出珠具为答。彭因出蜜,纵嗜群延旦属餍。报谢不一,得珠贝盈斗。又某氏忘其姓,亦随舶舟至蕃部。偶携陶瓷犬、鸡、提孩之属,皆小儿戏具者。登市,群儿争买。一儿出珠,相与贸易,色径与常珠不类。亦漫取之,初不知其珍也。舶既归,忽然风雾昼晦,雷霆轰吼,波涛汹涌,覆溺之变在顷刻。主船者曰:“吾老于遵海,未尝遇此变。是必同舟有异物。宜速弃以厌之。”相与诘其所有,往往皆常物。某氏曰:“吾昨珠差异,其或是也。”急启箧视之,光彩眩目,投之于波间,隐隐见虬龙攫孥以去,须臾变息。暨舶至止,主者谕其众曰:“某氏若秘所藏,吾曹皆葬鱼腹矣。更生之惠不可忘。”客各称所携以谢之。于是舶之凡货皆获焉。 因为这种商业的利润很大,所以不单是华商,就是中国的官吏,也利用他们雄厚的资本,以亲信充当商人来经营。《宋会要·职官》四四云: 至道元年三月,诏广州市舶司曰,“朝廷抚绥远俗,禁止末游,比来食禄之家,不许与民争利。如官吏罔顾宪章,苟徇财货,潜通交易,阑出徼外,私市掌握之珍,公行道中,靡虞薏苡之谤,永言贪冒,深蠹彝伦。自今宜令诸路转运司指挥部内州县,专切纠察。内外文武官僚,敢遣亲信于化外贩鬻者,所在以姓名闻”。 例如《宋史》卷二七七《张鉴传》云: 初(知广州张)鉴在南海,李庚夷为通判,谢德权为巡检,皆与之不协。二人密言鉴以赀付海贾往来贸市,故徙小郡。 这些华商由广州前往贸易的国家,现可考见的,为(1)交趾——《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二七三载熙宁九年二月壬申,诏,福建、广南人因商贾至交趾,或闻有留于彼用事者。…… (2)占城——《宋史》卷四八九《占城传》云: 庆历元年九月,广东商人邵保见军贼鄂邻百余人在占城。 又《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一三三载庆历元年八月庚申,广南东路转运司言,“商人邵保至占城国……” (3)大食——《岭外代答》卷二云: 中国舶商欲往大食,必自故临易小舟而往。 宋代中国的商人,除经营广州的海外贸易外,对于广州与国内各地相互间的贸易的经营,更其占有重要的地位。上引《独醒杂志》卷一○说“庐陵商人彭氏子,市于五羊”,可知广州与江西庐陵间的贸易,操于华商之手。又洪迈《夷坚丙志》卷一三说广州估客由海道贩货往沿海各地云: 绍兴八年,丹阳苏文罐为福州长乐令,获海寇二十六人。先是广州估客及部官纲者凡二十有八人,共僦一舟。舟中篙工柁师略相敌,然皆劲悍不逞,见诸客所赍物厚,阴作意图之。行七八日,相与饮酒大醉,悉害客,反缚投海中。独留两仆使爨。至长乐境上,双橹折。盗魁使二人往南台市之,因泊浦中以待。……两仆逸其一,径诣县告焉。...... 又《夷坚志补》卷二一说建康巨商经营广州与建康间的贸易云: 建康巨商杨二郎,本以牙侩起家。数贩南海,往来十有余年,累赀千万。淳熙中,…… 又《异闻总录》(撰人佚)卷一亦载此事云: 建康杨二郎,兴贩南海,往来十余年,累赀千万。淳熙中……二、宋代广州的国外贸易 (1)广州的进口贸易 《宋会要·职官》四四云: 市舶司掌市易南蕃诸国物货航舶而至者。初于广州置司……凡大食、古逻、阇婆、占城、勃泥、麻逸、三佛齐、宾同胧、沙里亭、丹流眉,并通货易。以金、银、缗钱、铅、锡、杂色帛、精粗瓷器市易香药、犀、象、珊瑚、琥珀、珠啡、宾铢、鼊皮、碡瑁、玛瑙、车渠、水精、蕃布、乌構、苏木之物。(《宋史》卷一八六《食货志》有相似的记载) 由此可知广州海外贸易的对手及输出入商品之一斑。在这些进口的商品中,尤以奢侈品为多。从当时的文献上看,广州是一个外国宝货的集中地。如《续资治通鉴长编》云: (景德四年七月甲戌,真宗)命内侍高品周文质为广州驻泊都监,谕之曰,“番禺宝货所聚……”(卷六六) (通判孔)勖在广州,以清洁闻。及被召,番酋争持献宝货。皆慰遣之。(卷七一) 又如《宋史》云: 知广州。……珍货大集。(卷二九八《马亮传》) 知广州。……南海饶宝货。(卷三四三《蒋之奇传》) 上(真宗)语近臣曰,“番禺宝货雄富……”。(卷四六六《张继能传》) 广州宝贝丛凑。(卷四七二《蔡京传》) 在由海外输入广州的奢侈品中,以真珠、犀角及象牙为最有名。《广东通志》卷九二载宋赵叔盎《千佛塔记》云: 南海,广东一都会也。海舶贾番,以珠犀为之货,丛委于地,号称富庶。 又《宋会要·蕃夷》四说大食人以象牙及犀角卖与广州市舶司(宋代象牙与犀角都是禁榷物,须卖与市舶司。见下一章)云: 绍兴元年十一月二十六日,提举广南路市舶张书言上言,“契勘大食人使蒲亚里进贡大象牙二百九株,大犀三十五株,见收管广州市舶库。象牙各系五十七斤以上,依例每斤估钱二贯六百文,约用本钱五万余贯。……” 其中尤以关于犀角的记载为多。如张世南《游宦纪闻》卷二云: 犀出永昌山谷及益州。今出南海者为上。……五羊、桂筦、桐城亦有之,往往皆来自蕃舶。 又王闢之《渑水燕谈录》卷八云: 犀之类不一。……来自舶上生大食者文如茱萸,理润而缀,光彩彻莹,甚类犬鼻。 其次,由外国输入广州的商品,尤以香药为最大宗。《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三一○载元丰三年朱初平的话云: 广州,外国香货及海南客旅所在。 又戴埴《鼠璞》云: 广通舶出香药。 又苏轼《东坡题跋》卷一云: 张广州《与妹仁寿夫人书》云,“广州真珠香药极有……” 宋代由海外输入广州的香药,种类甚多。兹就其著名者,列举如下: (1)龙涎香这是香药中最贵重的一种。《游宦纪闻》卷七说大食的龙涎香输入广州云: 诸香中龙涎最贵重,广州市直每两不下百千,次等亦五六十千。系蕃中禁榷之物,出大食国。……予尝叩泉广合香人。云,“龙涎入香,能收敛脑麝气,虽经数十载,香味仍在”。 又《岭外代答》卷七《龙涎》亦云: 大食西海多龙,枕石一唾,涎沫浮水,积而能坚。鲛人采之,以为至宝。新者色白,稍久则紫,甚久则黑。因至番禺,尝见之。不薰不莸,似浮石而轻也。今广州龙涎所以能香者,以用蕃栀故也。 (2)龙脑香唐慎微《经史证类备用本草》卷十三云: (苏颂《本草》)《图经》曰,“龙脑香……今惟南海舶贾客货之”。 又《宋史》卷四八九《三佛齐传》说该国纲首卖龙脑与广州市舶司云: (元丰)三年,广州南蕃纲首以其主管国事国王之女唐字书寄龙脑及布与提举市舶孙逈。逈不敢受,言于朝。诏令估直输之官,悉市帛以报。(《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三三○及《宋会要·职官》四四有相似的记载) (3)沉香叶宾《坦斋笔衡》(《说郛》卷一八)说登流眉的沉香贩人广州云: 范致能平生酷爱水沉香,有精鉴,尝谓:“广舶所贩之中下品,黎峒所产大块……皆为佳品……”大率沈水以万安东峒为第一品,如范致能之所详;在海外则登流眉片沈,可与黎东之香相伯仲。登流眉有绝品,乃千年枯木所结,如石柱、如拳、如肘、如凤、如孔雀、如龟蛇、如云气、如神山人物。焚一片则盈屋香雾,越三日不散。彼人自谓之无价宝。世罕有之,多归两广帅府及大贵势之家。 又《岭外代答》卷七云: 广东舶上生熟速结等香,当在海南笺香之下。 按这里说的“生结”、“熟结”等香都是沉香,因为沉香又可分为几类。蔡絛《铁围山丛谈》卷五云: 沉水香其类有四。谓之熟结,自然其间凝实者也。……谓之生结,人以刀斧伤之,而后膏脉聚焉,故言生结也。 (4)乳香本文第一章第二节引《粤海关志》说宋代广州市舶司所收乳香的数量远过于当时其他的舶港,可见输入广州的外国乳香之多。 (5)木香《经史证类备用本草》卷六说外国的木香输入广州云: 《图经》曰,“木香生永昌山谷。今惟广州舶上有来者,他无所出”。 《别说》云,“谨按,木香皆从外国来,即青木香也”。 (6)薰陆香陈敬《香谱》卷一说薰陆香经由大食、三佛齐等国贩人广州云: 叶廷珪云:(乳香?)一名薰陆,出大食国之南数千里深山穷谷中。其树大抵类松,以斤斫树,脂溢于外,结而成香,聚而为块。以象辇之,至于大食。大食以舟载易他货于三佛齐。三佛齐每岁以大舶至广与泉。广泉二舶视香之多少为殿最。 (7)蕃栀子这也是香的一种,龙涎所以能香完全靠它。《岭外代答》卷七说广州有大食蕃栀子出卖云: 蕃栀子出大食国,佛书所谓簷葡花是也。海蕃干之,如染家之红花也。今广州龙涎所以能香者,以用蕃栀故也。 (8)耶悉茗花高似孙《纬略》(《说郛》卷八)说外人将此花输入广州云: 耶悉茗花是西国花,色雪白。胡人携至交广之间,家家爱其香气,悉种植之。 (9)蔷薇露《宋史》卷四七二《蔡京传》说外人将蔷薇露贩人广州云: 广州宝贝丛凑,(蔡卞)一无所取。及徙越,夷人称其去,以薔薇露洒衣送之。 按蔷薇露又名蔷薇水,以大食国制造者为最佳。它输入广州后,广州人士曾加以仿制,但不及外来者。《铁围山丛谈》卷五云: 旧说蔷薇水乃外国采蔷薇花上露水,殆不然。实用白金为甑,釆蔷薇花蒸气成水,则屡采屡蒸,积而为香。此所以不败。但异域蔷薇花气馨烈非常,故大食国薔薇水虽贮琉璃缶中,蜡密封其外,然香犹透彻闻数十步,洒著人衣袂,经十数日不歇也。至五羊效外国造香,则不能得蔷薇,第取素馨茉莉花为之,亦足袭人鼻观;但视大食国真蔷薇水犹奴尔。 以上所述宋代由外国输入广州的香药,多偏于香这方面。它们固然有人药用的,但多半都是贵重的奢侈品,作为焚烧、薰衣、装饰及其他享乐之用。此外,在宋代输入广州的商品中,又有不少药物。兹就《经史证类备用本草》一书记载明确者,述之如下。 (1)卢会卷九引苏颂《本草图经》云: 卢会出波斯国。今惟广州有来者。 (2)阿魏卷九引《图经》云: 阿魏木生波斯国……或云取其汁和米豆屑合酿而成,乃与今广州所上相近耳。 关于阿魏的波斯原名及其产地,BertholdLaufer有详细的考证,见其所著sino—Iranica,P.。 (3)没药卷十三引《图经》云: 没药生波斯国。今海南诸国及广州或有之。 又夏德等以为“没”的广州音为mut,是阿拉伯语muFF的对音(见ChauJuKua,P.)。这也是没药输入广州的证明。 (4)葫芦巴卷十三云: 葫芦巴生广州。或云种出海南诸蕃,盖其国芦菔子也。舶客种莳于岭外亦生,然不及蕃中来者真好。 按Bretschneider说的葫芦巴即是阿拉伯所产的hulba(Laufer,Sino—Iranica,P.),故葫芦巴是由大食国(即阿拉伯)输入广州的。 (5)无名异卷三引《图经》云: 无名异出大食国,生于石上。今广州山石中及宜州南八里龙济山中亦有之。 (6)摩娑石赵汝适《诸蕃志》卷二说在广州的大食人有摩娑石者,辟药虫毒,以为指环。遇毒则吮之立愈。此固可以卫生。 按无名异及摩娑石两种药物,在当时少有而宝贵,除由海外输入广州外,在其他海港不易买到。沈括《补笔谈》云: 熙宁中,阇婆国使人入贡方物,中有摩娑石一块,大如枣,黄色,微似花;又无名异一块,如莲药。皆以金函贮之。问其人真伪何以为验。使人云,“摩娑石有五色。石色虽不同,皆姜黄汁,磨之汁赤如丹砂者为真。无名异色黑如漆水,磨之色如乳者为真”。广州市舶司依其言试之,皆验,方以上闻。……天圣中,予伯父吏书新除明州。章献太后有旨,令以舶船求此二物。内出银三百两为价值;如不足,更许于州库贴支。终任求之,竟不可得。 在宋代由海外输入广州的商品中,除上述的奢侈品及各种香药外,食物也是其中的一种。当时广州进口的食物,以槟榔为最多。在《宋会要·职官》四四太平兴国七年闰十二月诏令所列举的输入商品中,槟榔是其中的一种。又《岭外代答》卷八亦说交队等地的槟榔输入广州云: 槟榔生海南黎峒,亦产交趾。……海商贩之。琼管收其征,岁计居什之五。广州税务收槟榔税,岁数万缗。 按宋代广州一带的人士酷嗜槟榔,消耗槟榔的数量甚大。同书卷六云: 自福建下四川与广东西路,皆食槟榔者,客至不设茶,唯以槟榔为礼。其法……广州又加丁香、桂花、三赖子诸香药,谓之香药槟榔。唯广州为甚,不以贫富长幼男女,自朝至暮,宁不食饭,唯嗜槟榔。富者以银为盘置之;贫者以锡为之。昼则就盘更瞰;夜则置盘枕旁,觉即噉之。中下细民,一日费槟榔钱百余。有嘲广人曰,“路上行人口似羊”。言以蒌叶杂嘴,终日噍饲也。曲尽瞰槟榔之状矣! 又罗大经《鹤林玉露》卷一三云: 岭南人以槟榔代茶,且谓可以御瘴。余始至,不能食。久之,亦能稍稍。居岁余,则不可一日无此君矣。 又庄季裕《鸡肋编》卷中亦云: 广州……人食槟榔,唾地如血。北人嘲之曰,“人人皆吐血……” 由此可知宋代广州输入槟榔的数量一定很大,所以广州光是槟榔的税收,每岁也有数万缗之多。复次,黎朦子(即柠檬Lemon)也由海外输入广州。《岭外代答》卷八云: 黎朦子,如大梅。复似小橘,味极酸。或云,自南蕃来。番禺人多不用醯,专以此物调羹,其酸可知;又以蜜煎盐渍,暴干收食之。 此外,波斯枣也贩人广州。《经史证类备用本草》卷二三引《图经》云: 广州有一种波斯枣……舶商亦有携本国生者至南海,与此地人食之。云味极甘,似北中天蒸枣之类;然其核全别,两头不尖,双卷而圆,如小块紫矿。种之不生,疑亦蒸熟者。近亦少有将来者。 由上述,可知宋代广州海外贸易的对象为大食、三佛齐、占城等南洋一带的国家。其中尤以与大食贸易的数量为大,有好些商品如犀角、象牙及各种香药都是从那里输入广州,所以来广州从事贸易的大食商人(如上引《程史》所记的蒲氏)非常有钱。至于由这些国家输入的商品,则以真珠、犀角、象牙以及各种香药为主,其次又有食物如槟榔、黎朦子及波斯枣等。这里要注意的是:在这许多输入广州的商品中,多半属于原料的性质,甚少加工的制造品。其中可以说是工业制造品的,只有蔷薇露、蕃布等一些物品。 (2)广州的出口贸易 上一节引《宋会要·职官》四四说宋代广州在海外贸易时输出商品为“金、银、缗钱、铅、锡、杂色帛、精粗瓷器”等。又《宋史·食货志》云: 嘉定十二年,臣僚言:“以金银博买,泄之远夷,为可惜。”乃命有司止以绢、帛、锦、绮、瓷、漆之属博易。(卷一八五) 南渡三路(广南、福建、两浙)舶司岁入固不少,然金、银、铜、铁、海舶飞运,所失良多。(卷一八六) 由此可知,宋代广州的出口货物为五金(金、银、铜、铁、锡。为方便计,将铅亦归人此类商品内)、布帛(杂色帛、绢、锦、绮)、瓷器及漆器等。 以上各种出口货物,除五金中或有一部分属于原料外,全是工业制造品。事实上,在出口的五金中,大部分也都是工业制造品。如《宋会要·蕃夷》四说大食使人在华购买金银器物,由广州运返本国云: (绍兴)四年七月六日,广南东路提刑司言,“大食国进奉使人蒲亚里将进贡回赐到钱,置大银六百锭及金银器物匹帛。被贼数十人持刀上船,杀死蕃牧四人,损伤亚里,尽数劫夺金银等前去。已帖广州火急捕捉外,乞……” 至于铜器,广州输出更多。《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一一五载景祐元年十月丙戌权度支判官李甲言:“广南蕃舶多毀钱以铸铜器。请自今陈告者皆倍给赏钱,公人迁一资。”从之。 又《宋会要·刑法》二载嘉定十五年十月十一日,臣僚言,“国家置舶官于泉广,招徕岛夷,阜通货贿。……今积习玩熟,来往频繁,金、银、铜钱、铜器之类,皆以充斥外国……”。 在这些由广州输出的铜器中,现可考见的,有铜钟及铜瓦等物。《宋会要·蕃夷》四说广州的钟输往大食云: 真宗咸平元年八月,诏曰:“敕大食国王,先差三麻杰托舶主陁离子广州买钟,除纳外,少钱千三百余贯事:卿抚驭一方,恭勤万里,泛海常修于职贡,倾心远慕于声明,所言洪钟,虽亏估价,以卿素推忠恳,宜示优恩,特免追收,用隆眷注。所欠钟钱,已降敕命蠲放,故兹示谕。” 又楼鑰《攻娩集》卷八六《汪公(大猷)行状》说广州的铜瓦输往三佛齐云: 三佛齐请就郡铸瓦三万斤。舶司得旨,令泉广二州守臣监造付之。 关于其他工业品之由广州出口,在各种文献中,亦有零碎的记载。如《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三三○说彩帛由广州输往三佛齐云: (元丰五年十月甲子)广东转运副使兼提举市舶司孙回言:“南蕃纲首持三佛齐詹卑国主及管勾国事国主之女唐字书寄臣熟龙脑二百二十七两,布十三段。……前件书物,臣不敢受领。乞估直入官,委本库买彩帛等物,候冬舶回,报谢之。所贵通异域之情,来海外之货。”从之。(《宋会要·职官》四四有相似的记载) 又上引《宋会要·蕃夷》四亦说大食使人在华买有“匹帛”等物,由广州运送回国。复次,关于陶瓷器之由广州输出,上一章引的《独醒杂志》卷一○云: 又某氏忘其姓,亦随舶舟至蕃部。偶携陶瓷犬、鸡提孩之属,皆小儿戏具者。登市,群儿争买。 又《宋会要·刑法》二亦载嘉定十五年十月十一日,臣僚言:“国家置舶官于泉广,招徕岛夷,阜通货贿。彼之所阙者,如瓷器、茗、醴之属,皆所愿得。……” 除上述各种工业制造品外,宋代由广州输往外国的货物又有饮食品一項。上引一段记载“茗”、“醴”也是出口货物,由此可知茶及酒也由广州贩往外国。又《独醒杂志》卷一○说华商在广州购买石蜜,运往外国出售云: 庐陵商人彭氏子,市于五羊,折阅不能归。偶知旧以舶舟浮海,邀彭与俱,彭适有数千钱,谩以市石蜜发舟。 复次,骡马也是宋代广州的出口货物。《宋会要·蕃夷》四(又见《蕃夷》七)说骡马由广州运往占城云: 神宗熙宁元年六月四日,遣蒲麻勿等贡方物。赐物有差。奉占城蕃王杨卜尸利律陀般摩提婆表,乞买骡马一二匹,将回本土看玩。诏特赐白马二匹,开花鞔银鞍辔一副;所有骡,令就广州取便收买。 又《宋史》卷四八九《占城传》亦载此事云: 熙宁元年,其王杨卜尸利律陀般摩提婆遣使贡方物,乞市驿马。诏赐白马一(《会要》作“二”),令于广州买骡以归。 宋代广州的海外贸易,其输出的商品,除如上述外,这里要特别提出来说的,是铜钱的输出。这在当时是很受人注意的一个问题,曾经引起全国朝野上下的热烈讨论;所以除一般地叙述过各种出口货物以外,更特别地提出这一点来说。《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一三二载庆历元年五月乙卯,诏:“以铜钱出外界,一贯以上,为首者处死。其为从若不及一贯……广南、两浙、福建人配陕西。其居停资给者,与同罪。如捕到蕃人,亦决配荆湖、江南编管……”初权三司使公事叶清臣言:“朝廷务怀来四夷,通缘边互市。而边吏习于久安,约束宽弛,致中国宝货钱币,日流于外界。……”故于旧条,第加其罪。 又同书卷二六九载熙宁九年秋张方平论钱禁曰: 自熙宁七年颁行新敕,删去旧条,削除钱禁,以此边关重车而出,海舶饱载而回。……诸舟同舶旧制,惟广州、杭州、明州市舶司为买纳之处,往还搜检,条制甚严,尚不得取便至他州也。今日广南、福建、两浙、山东,恣其所往,所在官司,公为隐庇;诸系禁物,私行买卖,莫不载钱而去。钱本中国宝货,今乃与四夷共用!……盖自弛禁,数年之内,中国之钱,日以耗散。更积岁月,外则尽入四夷,内则恣为销毁,坏法乱纪,伤财害民,其极不可胜言矣。(《宋史》卷一八○《食货志》有相似的记载) 以上是北宋的情形。到了南宋,铜钱的出口更甚。《宋史·食货志》云: 南渡三路舶司岁入固不少,然金、银、铜、铁,海舶飞运,所失良多。而铜钱之泄尤甚。法禁虽严,奸巧愈密。商人贪利而贸迁,黠吏受赇而纵释,其弊卒不可禁。(卷一八六) 又自置市舶于浙,于闽,于广,舶商往来,钱宝所由以泄。是以自临安出门下江海,皆有禁。淳熙九年,诏:“广、泉、明、秀,漏泄铜钱,坐其守臣。”嘉定六年,三省言:“自来有市舶处,不许私发番船。”绍兴末,臣僚言:“泉、广二舶司及西、南二泉司遣舟回易,悉载金钱。四司既自犯法,郡县巡尉其能谁何!……”(卷一八○) 关于此事,《宋会要》记载得更为详细。《职官》四四载绍兴十一年十一月二十三日,臣僚言:“广东、福建路转运司遇船舶起发,差本司属官一员,临时点检,仍差不干碍官员觉察至海口,俟其放洋,方得回归。如所委官或纵容般载铜钱,并乞显罚,以为慢令之戒。”诏下刑部立法。刑部立到法,“诸舶船起发(贩蕃及外蕃进奉人使回蕃船同),所属先报转运司,差不干碍官一员,躬亲点检,不得夹带铜钱出中国界。仍差通判一员覆视,候其船放洋,方得回归。诸舶船起发,所委点检官覆视官同纵容夹带铜钱出中国界首者,依知情引领停藏负载人法;即覆视官不候其船放洋而辄回者,徒一年”。从之。 又《刑法》二云: (嘉定十年)十一月二十九日,臣僚言:“臣{入耳}……铜钱之消耗,原于透漏之无涯。乞行下庆元、泉、广诸郡,多于舶船离岸之时,差官检视之外,令纲首重立罪状,舟行之后,或有告首败露,不问缗钱之多寡,船货悉与拘没。仍令沿海州郡多出膀示于湾陕泊舟去处,重立赏格,许人缉捉。每获到下海铜钱一贯,酬以十贯之赏,仍将犯人重与估藉,庶几透漏之弊少革。”从之。 (嘉定)十五年十月十一日,臣僚言:“国家置舶官于泉、广,招徕岛夷,阜通货贿。……今积习玩熟,来往频繁,金、银、铜钱、铜器之类,皆以充斥外国……。”又言,“蕃夷得中国钱,分库藏贮,以为镇国之宝。故入蕃者非铜钱不往。而蕃货亦非铜钱不售。利源孔厚,趋者日众。今则沿海郡县寄居,不论大小,凡有势力者则皆为之。官司不敢谁何,且为防护出境。铜钱日寡,弊或由此。傥不行严行禁戢,痛加惩治,中国之钱将尽流入化外矣!乞亟赐行下,应与(兴?)贩铜钱下海入蕃者,别立赏格,许人指告;命官追官勒停,永不叙理;百姓籍没家财,重行决配”。并从之。 以上各种文献所言,宋代的铜钱不单由广州出口,且同时又由其他海港输出。此外,又有专说铜钱由广州出口的。如《宋会要·职官》四四云: (绍兴)二十七年六月一日,宰执进呈户部措置到广南铜钱出界事。 (淳熙)六年正月二十二日,诏前(知)广州郑人杰特降二官。以人杰任内透漏铜钱银宝过界,故有是命。 除上述外,关于铜钱出口的记载,还有许多。如《宋史》云: (绍圣元年)十二月辛未,申严铜钱出外界法。(卷一八《哲宗纪》) (绍兴三年十一月)甲戌,禁……以铜钱出中国。(卷二七《高宗纪》) (绍兴二十八年)九月辛未,定铜钱出界罪赏。(卷三○《高宗纪》) (乾道七年三月)乙酉,立沿海州军私赍铜钱下海船法。(卷三四《孝宗纪》) (嘉定十六年八月)癸未,申明舶船铜钱之禁。(卷四○《宁宗纪》) (端平元年六月)癸巳……禁毁铜钱作器用并贸易下海。(卷四一《理宗纪》) 端平元年,以胆铜所铸之钱不耐久,旧钱之精致者泄于海舶,申严下海之禁。(卷一八○《食货志》) (王居安)言,“蕃舶多得香犀象翠,崇侈俗,泄铜镪,有损无益。宜遏绝禁止。”(卷四○五《王居安传》) 又《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一四载开宝六年三月,禁铜钱不得入蕃界及越江海至化外。 又李觏《李直讲文集》卷一六《富国策第八》云: 至于蛮夷之国,舟车所通,窃我泉货,不可不察。 又洪遵《泉志·序》云: 呜呼,泉用于世久矣!其始作之,艰且劳者也。不幸则为……又不幸则为金工所铄,童孺所镳,夷舶蛮舶之所负。其不耗也危乎殆哉! 又《诸蕃志》卷上《阇婆国》云: 此番胡椒萃聚,商舶利倍蓰之获,往往冒禁,潜载铜钱博换。朝廷屡行禁止兴贩。番商诡计,易其名曰苏吉丹。 这许多关于宋代铜钱出口的记载,虽然没有明说全是由广州输出,但广州在宋代既然是最大的一个对外贸易港(见第一章第二节),那么,在这些出口的铜钱中,必有一大部分由广州输出,我们是可以断言的。 桑原骘藏在《蒲寿庚考》第一章中对于宋代铜钱的输出,亦曾加以研究。其所根据材料,偏于外国方面,兹摘录如下: 宋时中国输出海外之品,以金、银、铜钱、绢、瓷器等为主;海外输入者,以香药、珠、玉、象牙、犀角等为主。贸易既盛,钱货遂涌涌外溢。当时宋之铜钱,东自日本,西至伊士兰教国,散布至广。 日本自藤原时代之末期,宋钱输入颇夥。……南洋一带,宋钱之散布更多;久而久之,遂成彼地之通货(Crawfurd《印度各岛解释字汇》九十四页)。明初马欢《瀛涯胜览·爪哇国》条,“买卖交易,行使中国历代铜钱”。又《旧港国》条,“市中交易,亦使中国铜钱”。元代殆无铸钱事,此等中国铜钱,大半当为宋钱也。 千八百二十七年,星嘉坡掘得中国铜钱,多数为宋钱(Crawfurd,Ibid,九十四页)。千八百六十年顷,爪哇有地方曰Djokjokert0,掘得中国铜钱三十枚,亦过半为宋钱(Schlegel《地名考》,一八九九年《通报》二六五页)。南印度之马八儿,宋末元初时,为中国商船往来频繁之地,其海岸一带,自前世纪中叶以来,时时有中国铜钱出土(YuleandCordier《马哥孛罗》二卷三三七页)。虽无委细报告,其中宋钱当甚多也。千八百八十八年,英人于非洲东岸之桑给巴尔(即赵汝适《诸蕃志》之层拔国,见一八九四年《通报》三十四页及《赵汝适》一二六页),掘土得宋代铜钱。最近则千八百九十八年,德人于同州东岸索马里滨海之Miigedoshn,亦掘得宋代铜钱(Hirth《东非洲之最初汉迹》,一九○五年I.A.0.S.五五及五七页)云。 观以上事实,可知宋人所云,“钱本中国宝货,今乃与四夷并用”,并非夸语矣。 由此可知宋代铜钱在海外分布区域之广。这许多铜钱,固然不单由广州,而且由其他海港输出。不过因为广州在当时是中国最大的对外贸易港,而地理上又与南洋一带的国家距离最近,故我们可以推知,在这些输出的铜钱中,一定有许多由广州出口。 综括上述,可知宋代广州的海上贸易,其输出商品以工业制造品为主。五金、布帛、瓷器以及漆器,都是当时主要的出口工业品。就是出口的饮食品,如茶、酒及石蜜,也多半是加工制造过的。复次,宋代广州出口贸易的另一特点为铜钱之大量输出。其结果,宋代以后南洋一带的国家多半采用这些铜钱作为交易上的媒介。而这些铜钱自然也是工业制造的产物。所以在宋代的国际贸易中,广州实是以工业国家的代表的资格来与工业落后的国家互相交易。(3)宋代广州的贸易均衡及铜钱流出的影响 综括上述,可知宋代广州的对外贸易,为以我国出产的工业品(包括贵重的奢侈品,如金银器等)与南洋一带国家出产的奢侈品及原料交换;而其中有一特色,即中国的铜钱大量地运往外国。这种现象,使我注意到这个问题:宋代广州的对外贸易是否人超?普通的说法,自然以为这是对外贸易人超的结果,因为一般说来,铜钱(这是当时最主要的货币)所以要运往外国,是因为对外贸易人超,须运铜钱出口以弥补此种人超差额的原故。可是,缜密考虑的结果,我可不能同意这种论断。其理由可列举如下。 (1)中国是铜的大量生产地,而南洋各国则缺乏此种出产,故铜钱除了是货币以外,同时又可当作商品来输出,因为铜在当时中国市场的价格比外国为贱;这有如出产大量金银的国家(如墨西哥等),其人民从事于矿业者既多,从事于工农业者自少,从而不得不输出金银以交换外国的工农产品。按中国产铜的地方很多,尤以南方为甚。《宋史》卷一八五《食货志》云: 铜产饶、处、建、英、信、汀、漳、南剑八州,南安、邵武二军,有三十五场,梓州有一务。 至于铜的产额,更在各种矿产产额之上。兹据《宋史》卷一八五《食货志》列举元丰元年全国各种矿产产额如下,以资比较:金两银两铜斤铁斤铅斤锡斤水银斤朱砂斤14两有奇 反观当时南洋一带的国家,情形正正相反。她们本土大都没有铜的出产,故交易不用铜钱,只以金银等物作交换媒介。兹列举《宋史》卷四八九《外国传》关于矿产及货币的记载,以作证明: (占城)土地所出……金银铁锭等物。 (三佛齐)无缗钱,土俗以金银贸易诸物。 (阖婆)出金银……剪银叶为钱博易。官以粟一斛二斗博金一钱。 (南毗)杂金银为钱。 (丹流眉)贸易以金银。 此外,关于当时大食国的矿产及货币,《宋史·外国传》没有记载,但洪遵《泉志》卷一○说大食使用金钱及银钱云: 右大食国钱(按原书有图——汉)。《广州记》曰:“生金出大食国。彼方出金最多,凡诸贸易,并使金钱。”《国朝会要》曰:“大中祥符九年十一月,大食国以金钱银钱各千文入贡。”余按此钱以金为之。 由此可知,在宋代中国是铜产最富的国家,而南洋各国是铜产最缺乏的国家。前者铜的供给既多,价格自然低廉;后者铜的供给既少,价格自然昂贵。两地铜的市场价格相差既大,商人将铜由中国贩往海外时,除了运费的开支外,仍有很大的利润。利之所在,追求利润的中外商人自然争着去经营。如《宋会要·刑法》二载嘉定十五年十月十一日,臣僚……又言:“蕃夷得中国钱,分库藏贮,以为镇国之宝。故入蕃者非铜钱不往,而蕃货亦非铜钱不售。利源孔厚,趋者日众。今则沿海郡县寄居,不论大小,凡有势力者则皆为之。……” 又如《诸蕃志》卷上《阇婆国》云: 此番胡椒萃聚,商舶利倍蓰之人,往往冒禁,潜载铜钱博换。 (2)就当时进出口商品的性质而论,广州的海外贸易没有人超的理由。一般地说,工业发达的国家与工业落后的国家贸易,总是前者出超,后者人超的。前者的出口货多半为加工制造过的工业品,人口货多半为原料;后者则正正相反。结果前者除向后者收回其出口工业品所用的原料的价钱外,同时又得到一大笔加工制造的费用,所以前者往往出超,后者则人超。现今中国与欧美工业化国家贸易的情形,便是例证。就此论点来观察当时的海外贸易,广州实没有人超的理由。因为如上所说,中国输出的多半为工业制造品(包括贵重的奢侈品,如金银器等),就是其中有一些饮食品,也是加工制造的;反之,由海外输人的,虽有不少的奢侈品,但它们大半都是原料,加工制造过的简直寥寥无几。 关于此点,我们如将辽、夏、金等国与两宋贸易的情形来加以比较,更易明了。当时辽、夏、金等国的工业都很落后,而两宋则是工业发达的国家。所以北宋与辽夏等国贸易时,其出口货多半为工业品,其人口货多半为原料及食料。如《宋史》卷一八六《食货志》云: (景德)三年,诏民以书籍赴沿边榷场(与契丹)博易,非九经书疏,悉禁之,凡官鬻物(犀、象、香药及茶)如旧,而增缯、帛、漆器、秔糯。所入者有银、钱、布、羊、马、棄驰。 西夏自景德四年于保安军置榷场,以缯、帛、罗、绮易驼、马、牛、羊、玉、毡毯、甘草,以香药、瓷、漆器、姜、桂等物品易蜜、蜡、麝脐、毛褐、羱羚角、硇砂、紫胡、苁蓉、红花、翎毛。 由这些输出人商品的性质看来,北宋与辽夏贸易是不会人超的。到了南宋,金国因为占有中国的北部,其工业固然比辽夏好些,但却远不如南宋的发达,故南宋与金的贸易,其进出口货的性质在大体上与上述差不了很多。所以日人加藤繁断定南宋与金贸易时,南宋为出超,金为人超。(见加藤繁《宋金贸易论》,《史学杂志》昭和十二年一月号;周乾澡译文载《食货半月刊》第五卷第九期)可是,虽然是这样,两宋的铜钱却大量地运往辽夏及金。关于北宋铜钱之运往辽国,《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一七一载皇祐三年十一月辛亥定州路安抚使司言,“雄州、广信、安肃军雄(榷?)场,北客市易,多私以铜钱出境……”。 又《宋会要·刑法》二载政和元年四月十五日,刑部奏:“定州乞申严,自今将铜钱出雄、霸州、安肃、广信军等处,随所犯刑名上,各加一等断罪。”从之。 其结果,辽国所用钱多为北宋所铸。《宋史》卷一八○《食货志》云: 供备库使郑价使契丹还,言其给舆箱者钱,皆中国所铸。乃增严三路阑出之法。 复次,关于北宋铜钱之运往西夏,《宋史》卷一八○《食货志》云: 西北边内属戎人,多赉货帛于秦阶州易铜钱,出塞销铸为器。 又载张方平的话云: 自熙宁七年颁行新敕,删去旧条,削除钱禁,以此边关重车而出……闻沿边州军钱出外界,但每贯收税钱而已。 所谓“边关重车而出”,指的是宋钱由陆路大量地运往辽夏等国。到了南宋,铜钱之输往金国,数量更多。《宋史》卷一八○《食货志》云: 绍兴末,臣僚言:“……南北贸易,缗钱之入敌境者,不知其几。” 又同书卷三七三《洪皓传》云: 林安宅以铜钱多入北境,请禁止之。 又《宋会要·刑法》二云: (乾道)三年三月二日,臣僚言:“伏见钱实(宝?)之禁,非不严切。而沿淮冒利之徒,不畏条法,公然般盗出界,不可禁止。……” (六年)十月二十八日,权发遣盱眙军龚鋈言:“每年津发岁弊(币?)过淮交割,其随纲军兵及使臣等曰(目?)不下四五十人,往往循习年例,私传钱宝出界。并夹带私商,不容搜检。……” 又同书《职官》五一载庆元元年六月二十九日,臣僚言:“铜钱透漏,法禁不行。今朝廷见议两淮铁钱,未有成说。虽铁钱不得过江,而铜钱过淮常自若也。每岁使人出疆,一行随从颇众,谁不将带铜钱而往?不知几年于此矣!……” 由此可知,两宋与辽、夏、金等国贸易,虽不至于人超,铜钱却大量地运往这些国家。以此例彼,铜钱之由广州运往海外,当然也是同样的情形。所以我们对于宋代由广州出口的铜钱,只能看作因两国的市场价格相差很大而交易的商品,不能当作平衡国际贸易差额的工具来看待。 (3)中国政府如认为当时国际贸易老是人超,每年须输出大量铜钱,于本国不利,在当时国力不如现在那样衰微的情形下,大可以闭关不与外国贸易。可是事实却不如此,当时政府(尤其是广州政府)反为积极地奖励外国贸易,如第一章第二节所说;可见有利的贸易差额是在我而不在彼。 至于两宋政府所以屡次禁钱输出,亦自有其理由。铜钱流出的结果,对于国计民生的影响实在很大。这可分开北宋及南宋时期来说。北宋时,虽有交子,但只流通于四川;陕西河东一带,虽亦曾行使过,但为期甚短(见朱楔《两宋信用货币之研究》,《东方杂志》第三十五卷第五、六号)。故北宋时纸币的势力不大,货币以铜钱为主。在这时期,铜钱流出要发生什么影响呢?最主要的结果是商业衰敝,百货不通。如《宋史》卷一八○《食货志》载张方平论铜钱流出的话云: 比年公私上下,并苦乏钱,百货不通,人情窘迫,谓之钱荒。 又《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一三二载叶清臣的话云: 朝廷务怀来四夷,通缘边互市。……致中国宝货钱币日流于外界。比年县官用度既广,而民间货易不通。 又李觏《李直讲文集》卷一六《富国策·第八》云: 钱少则重,重则物轻……物轻则货或滞。 接着李觏又说钱少的主要原因云: 至于蛮夷之国,舟车所通,窃我泉货,不可不察。 为什么钱少(铜钱流出的结果)便商业凋弊,百货不通呢?按照货币数量学说,物价之大小与货币流通之多寡成正比例。宋代的主要货币是铜钱。铜钱流出太多,在本国流通的数量自少,从而物价便大大地跌落。上面李觏说,“钱少则重,重则物轻”,就是这个意思。又张方平论铜钱流出的影响云: 钱不可得,谷帛益贱。(《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二七七) 按照商业循环(businesscycles)的学说,在繁荣时期,物价涨高,同时货物又畅销;在恐慌及衰落时期,物价下落,同时货物又滞销。这是因为物价跌落时,商人及制造家怕亏本,不敢存货或制货太多的原故。所以李觏说:“物轻则货或滞。”这亦即是说,因为钱少,致物价跌落,故货物不能畅销,从而商业凋敝。复次,铜钱既是当时最主要的交换媒介,铜钱因流出而在国内流通数量减少,在交易上自然要感到周转不便,从而交易数量大减。上引张方平的话,“比年公私上下,并苦乏钱,百货不通”,便是此意。所以北宋铜钱流出的结果,钱在国内流通的数量便要减少,从而商业凋敝,百货滞销。 到了南宋,铜钱流出的影响,与北宋异。在这时,纸币流通遍于全国。其名称有种种的不同:“行在会子”行于两浙、福建、江东、江西;“川引”行于四川、陕南;“淮交”行于淮南;“湖会”行于湖广(见朱偰《两宋信用货币之研究》)。此时纸币对于全国人民经济生活的影响,可以说是普遍而深刻。纸币的价值,须有相当的铜钱作准备金,以便纸币价落时即出钱收回,才能维持;否则纸币价值便要下跌,不便行使了。《宋史》卷一八一《食货志》云: 昔高宗因论四川交子,最善沈该称提之说;谓宫中常有钱百万缗。如交子价减,官用钱买之,方得无弊。 又戴埴《鼠璞》云: 自商贾惮于般挈,于是利交子之兑换。故言楮者则曰秤提,所以见有是楮,必有是钱以秤提之也。 又《宋史》卷四三○《李燔传》云: 燔又入劄争之曰:“钱荒楮涌,子母不足以相权。不能行楮者,由钱不能权之也。……” 可是南宋铜钱大量流出的结果,发行纸币的准备金因国内铜钱流通额的减少而减少,从而纸币遂不能维持原来的价值而大大跌价。《宋会要·刑法》二云: (嘉定十年)十一月二十九日,臣僚言:“臣闻楮币之折阅,原于铜钱之消耗;铜钱之消耗,原于透漏之无涯……。” 十二年六月二十八日,都省言:“勘会见钱稀少,会价渐至低减,访闻日来皆由铜钱下江,并番舶偷载,与夫越界贩卖出外……。” 又同书《职官》四三云: 嘉定十五年七月二十二日,臣僚言,“铜钱浸少,楮券浸轻,不可不虑。夫铜为有限……商贾般载,散之外境,安得而不耗?……” 又《宋史》卷一八○《食货志》云: (淳祐)十年,以会价低减,复申严(铜钱)下海之禁。 又真德秀《真文忠公文集》卷三二《馆职策》云: 楮币曰轻,本由钱乏。厥今渗漏,非止一涂。有如……阑出于边关,上下共知矣。 纸币价值降低的结果,以纸币为交换媒介的商品的价格遂大大的上涨。如《续文献通考》卷七载景定五年十二月的诏令有云: 物贵原于楮轻。 又魏了翁《鹤山大全文集》卷一九《第四劄》云: 重以楮币泛滥,钱荒物贵,极于近岁。 因此,铜钱流出的影响,南宋与北宋正正相反。北宋时,铜钱因流出而减少,遂致物价(以铜钱表示)跌落;南宋时,铜钱因流出而减少,遂致纸币的准备金减少,从而纸币低折,物价(以纸币表示)反而昂贵。故《宋史》卷一八○《食货志》载淳祐八年陈求鲁的话云: 急于扶楮者……不思患在于钱之荒……夫钱贵则物宜贱,今物与钱俱重,此一世之所共忧也。 所谓钱贵则物贱,是北宋铜钱流出的影响;所谓“物与钱俱重”,是因为南宋使用纸币,铜钱因流出而减少,从而纸币价值跌落,故钱少反而使物价昂贵。不过无论物价因铜钱流出而跌落或上涨,对于人民的经济生活都有很恶劣的影响,我们是可以断言的。为着要除去这种恶劣的影响,所以两宋政府屡有禁止铜钱出口的措施。三、宋代广州的国内贸易(1)政府对于广州的外货贸易之经营 宋代由海外输入广州的商品,如何分配于国内各地?关于此种贸易的经营,可大别为两部分:一部分由政府专卖,在广州收买后,派人运至各地出售;一部分则由商人从广州贩往国内各地。大约利润较大的外货,都由政府专卖,以便丰裕国库,而免利润入于私人之手。现在先说政府对于这种买卖的经营。 宋代的中外商人将外货运抵广州时,由广州市舶司抽解其一部分,复收买若干,然后听其在市场上自由买卖;如果这些货物是政府规定的专卖品,则完全由政府收买。朱或《萍洲可谈》卷二云: 凡舶至,帅漕与市舶监官,莅阅其货而征之,谓之“抽解”。以十分为率,真珠龙瑙凡细色抽一分,碡瑁苏木凡粗色抽三分外,官市各有差,然后商人得为己物。象牙重及三十斤,并乳香,抽外尽官市,盖榷货也。 所谓“榷货”是专利品或专卖品的意思。曾三异《因话录》(《说郛》卷一九)石: 榷货非扬榷之义。榷,独木桥也,乃专利而不许他往之义。 按宋代的榷货,据太平兴国七年闰十二月及大中祥符二年八月九日两次诏令(均见《宋会要·职官》四四)所载,共有十种,即碡瑁、象牙、犀角、宾铁、鼊皮、珊瑚、玛瑙、乳香、紫矿及输石。其中尤以乳香的收买,获利最大。《宋会要·职官》四四载绍兴三年七月一日,诏广南东路提举市舶官,“今后遵守祖宗旧制,将中国有用之物,如乳香药物及中国民间常使香货,并多数博买。内乳香一色,客算尤广,所差官自当体国,招诱博买”。至于政府所用以收买这些外货的本钱,称为折博本钱、博易本钱或市舶本钱。这些本钱,很少是见钱(即铜钱),而是出口的各种货物。《萍洲可谈》卷二云: 凡官市价微,又准他货与之…… 又《宋史》卷一八五《食货志》云: 嘉定十二年,臣僚言,“以金银博买,泄之远夷,为可惜”。乃命有司止以绢、帛、锦、绮、瓷、漆之属博易。 这里要注意的是:政府收买外货所规定的价格较外货在市场上自由买卖的为低,所以政府常获大利,而商人则常亏本,或获利较小。《萍洲可谈》卷二云: 凡官市价微,又准他货与之,多折阅,故商人病之。 又《宋会要·职官》四四云: (绍兴十六年)九月二十五日,宰执进呈广南市舶司缴进三佛齐国王寄市舶官书,且言,“近来商贩乳香,颇有亏损”。 (开禧)三年正月七日,前知南雄州聂周臣言,“泉广各置舶司,以通蕃商。比年蕃船抵岸,既有抽解,合计从便货卖。今所隶官司,择其精者售以低价。诸司官属,复相嘱托,名曰和买。获利既薄,怨望愈深……”。 广州市舶司以官定价格收买到进口外货后,其中一部分即按照市场上通行的价格在当地出卖。《宋会要·职官》四四载崇宁四年五月二十日,诏,“每年蕃舶到岸,应买到物货,合行出卖,并将在市实直价例,依市易法通融收息,不得过二分”。从广南提举市舶司请也。 但大部分则连同抽解的外货,运往当时政治中心的汴梁。《宋会要·职官》四四云: (天圣)五年九月,(诏?),“自今遇有舶船到广州,博买香药,及得一两纲。旋具闻奏,乞差使臣管押”。 神宗熙宁四年五月十二曰,诏,“应广州市舶司每年抽买到乳香杂药,依条计纲,申转运司,召差广南东西路得替官往广州交管押上京送纳……”。 这些由广州运往汴梁的外货,就其性质大致分为粗色及细色两类,而分为一纲一纲的运往。至于体积及重量太大而价值又小的外货,则因负担不起巨额的运费而不运往汴梁,留在广州出卖。《宋会要·职官》四四载建炎元年十月二十三日,承议郎李则言:“闽广市舶旧法:置场抽解,分为粗细二色,般运入京。其余粗重难起发之物,本州打套出卖……。” 关于粗色及细色的外货的名称,这一段文字又接着说: 旧系细色纲,只是真珠龙脑之类,每一纲五千两。其余如犀、牙、紫矿、乳香、檀香之类,尽是粗色纲,每纲一万斤。……大观以后,犀、牙、紫矿之类,皆变作细色。(《宋史》卷一八六《食货志》有相似的记载) 复次,关于这些外货运往汴梁所走的道路,《宋史》卷一七五《食货志》云: 广南金、银、香药、犀、象百货陆运至虔州,而后水运。 按:《食货志》这段记载未免过于简略。事实上,由广州出发的外货,并不是一直陆运至虔州,因为由广州到南雄一大段是有水路可通的,需要陆运的只是大庾岭一小段而已。《宋史》卷二六三《刘熙古传》云: 岭南陆运香药入京,诏(刘)蒙正往规画。蒙正请自广韶江溯流至南雄;由大庾岭步至南安军,凡三铺,铺给卒三十人;复由水路输送。 过了大庾岭后所走的水路是赣江、长江、淮河及汴河。因此,在宋代由广州运外货至当时大消费中心的汴梁(汴梁是大消费中心的理由,见拙著《北宋汴梁的输出入贸易》)大半有便利的水道可通;其中须走陆路,只是大庾岭一小段。所以由于下列宋代大庾岭道路积极开发的记载,我们可推知这条商道(由广州到汴梁等地)在当时的繁荣,同时亦可推知广州与国内各地贸易的发达。《宋史》卷三二八《蔡挺传》云: 蔡挺,字子政……越数岁,稍起知南安军,提点江西刑狱,提举虔州监。自大庾岭下,南至广,驿路荒远,室庐稀疏,往来无所芘。挺兄抗(字子直)时为广东转运使,乃相与谋,课民植松夹道,以休行者。 又王巩《闻见近录》亦记蔡氏兄弟对于此路的整顿云: 庾岭险绝闻天下。蔡子直为广东宪,其弟子正为江西宪,相与协议,以砖凳其道。自下而上,自上而下,南北三十里,若行堂宇间。每数里,置亭以憩客。左右通渠,流泉涓涓不绝。红白梅夹道。行者忘劳。予尝至岭上,仰视青天如一线;然既过岭,即青松夹道,以达南雄州。 宋代由广州输入的外货,政府加以收买,运往汴梁后,它们遂在汴梁出卖。《宋会要·食货》三六载太平兴国二年三月……诏……先是外国犀、象、香药充牣京师,置官以鬻之。因有司上言,故有是诏。 北宋初年,在汴梁出卖这些外货的机关名叫榷易院。同书《食货》五五云: 太平兴国中,以先平岭南,及交趾海南诸国连岁入贡,通关市,商人岁乘舶贩易外国物,自三佛齐、勃泥、占城犀、象、香药珍异之物充盈府库,始议于京师置香药(榷)易院,增香药之直,听商人市之。命张逊为香药库使主之。岁得钱五十万贯。大中祥符二年二月,拨并入榷货务。 关于此事,《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一八亦有记载,但“榷易院”改作“榷药局”: (太平兴国二年正月乙亥)香药库使高唐张逊建议,请置榷药局,大出官库香药宝货,稍增其价,许商人入金帛买之,岁可得钱五十万贯,以济国用,使外国物有所泄。上然之。一岁中果得三十万贯。自是岁有增羡,卒至五十万贯。 此外,榷易院还有其他名称。《宋史》卷二六八《张逊传》作“榷易署”;同书卷一八六《食货志》作“榷署”。除榷易院外,榷货务也是在汴梁出卖外货的机关,在北宋初年与榷易院同时存在。《宋会要·食货》五五云: 至道二年十一月,诏榷货务博卖香药收钱帛,每月分十次送纳。 真宗咸平二年九月,诏榷货务招诱客人将钱银绸绢入中,并卖象牙。令香药库将合出卖第一等牙品配支拨。 (景德元年)闰九月,诏榷货务所卖紫赤矿香药,令依市实价出卖,不得亏官。 关于榷货务所在地点及职务,同书《食货》五五又云: 榷货务旧在延康坊,后徙太平坊。掌受商人便钱给券及中茶盐,出卖香药象货之类。 按上引《宋会要·食货》五五曾说,榷易院于“大中祥符二年二月,拨并人榷货务”。由此可知,在北宋初年,榷货务与榷易院同时存在,都在汴梁出卖外货;其后则榷易院被归并人榷货务,只由后者出卖外货。例如同书《食货》五五载大中祥符二年八月,诏榷货务,“客便纳金银钱帛粮草,合支香药象牙者,于香药库拨请还客……”。 以上所述,都是北宋初年的记载。北宋中叶以后,政府也是一样的在汴梁出卖外货,以佐国用。《宋史》卷一八六《食货志》云: 天圣以来,象、犀、珠、玉、香药宝货充初府库。尝斥其余,以易金帛刍粟。县官用度,实有助焉。 上述政府在汴梁出卖的外货,除因汴梁是当时的大消费中心,一部分由当地人士消耗外,其中一部分又由客商运往他处出卖。上引《宋会要·食货》五五各段记载,多说榷货务将香药、犀、象等物卖与“客”或“客人”。这些在汴梁购买外货的商人既被称为“客”,买货后当然是将货贩运至别处出卖的。复次,汴梁政府又派人运这些外货到边境的榷场,以与辽及西夏等国博易。(关于北宋汴梁的外货之贩往各地及辽夏等国,请参看拙著《北宋汴梁的输出入贸易》) 这里还要注意的,是政府因经营此种外货的买卖而得的利润之大。关于政府因此而得的利润,虽然没有精确的数字可供参考,我们却可根据其他材料来加以推论。上边曾说,政府在广州收买外货所规定的价格较外货在市场上自由买卖的为低。及运往汴梁后,据上引《宋会要·食货》五五及《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一八所载,政府却增高价格然后出卖。就是不运往汴梁,而在广州当地出卖,据上引《宋会要·职官》四四所载,政府也是按照当时市场上的高价而不是按照收买时的低价出卖的。政府这样买贱卖贵的结果,自然是可以得到一大笔收入的。所以上引《宋史》卷一八六《食货志》说政府经营此种买卖的结果云: 县官用度,实有助焉。 以上所述,都是北宋政府买卖由广州输入的外货的情形。到了南宋,因为政治中心由汴梁南转杭州(当时称为“行在”),政府在广州收买到的外货也运往杭州出卖。如《宋会要·职官》四四云: (乾道)七年十月十三日,诏:“今后广南市舶司起发粗色香药物货,每纲以二万斤正、六百斤耗为一纲。依旧例支破水脚钱一千六百六十二贯三百三十七文省。限五个月到行在交纳。……”(淳熙)二年二月二十七日,户部言:“……今措置,欲令福建、广南路市舶司,粗细物货并以五万斤为一全纲,福建限三月程,广南限六月程到行在。……”从之。 这时由广州运外货往杭州,走的多半为海道;因为这时海上交通较前发达,而广州及杭州的位置又均在海岸附近。所以上面引文说运输外货时止支“水脚钱”,下引《宋会要·刑法》二亦说“海运以达中都”。复次,我们要注意的是:政府在广州买到的外货,不完全运往杭州,其中一部分就在广州当地出卖。这在下列三种情形之下全都实现: ①虽然海运用费较廉,粗重而价较贱的外货,因不能负担运费,便不运往。如《宋会要·刑法》二载嘉定十五年十月十一日,臣僚……又言:“泉、广每岁起纲,所谓粗色,虽海运以达中都,然水脚之费,亦自不赀。今外帑香货充斥,积压陈腐,几为无用之物。臣以为当令舶司就地变卖,止以官券来输左帑。”……并从之。 ②物品太多,运往杭州后不易卖出,便留在广州出卖。如《宋会要·蕃夷》四说政府在广州收买到的象牙犀角太多,只以一半运往杭州,其余一半则在广州出卖云: 绍兴元年十一月二十六日,提单广南路市舶张书言上言:“契勘大食人使蒲亚里进贡大象牙二百九株,大犀三十五株,见收管广州市舶库。象牙各系五十七斤以上,依例每斤估钱二贯六伯文,约用本钱五万余贯。数目稍多,难以转变,乞起发一半,将一半就便搭息出卖给还。”诏拣选大象牙一百株、犀二十五株起发赴行在,准备解笏造带,宣赐臣僚使用。余从之。 又据上引《宋会要·刑法》二,中央政府所以“令舶司就地头变卖”,“外帑香货充斥,积压陈腐”,在杭州不易卖出,也是其中原因之一。 ③杭州一带人士不大用得着的外货,因运杭后不易卖出,便留在广州出卖。如《宋会要·职官》四四载绍兴八年七月十六日,臣僚言:“广南……市舶司抽买到市舶香药物货……缘合起发内,尚有民间使用稀少等名色,若行起发,窃虑枉费脚乘得亏损官钱。”诏令逐路市舶司,如抽买到和剂局无用并临安府民间使用稀少物货,更不起发本色,一面变转价钱,赴行在库务送纳。 政府将这些外货由广州运杭后,将作如何处置?这些外货,除如上引《宋会要·蕃夷》四及《职官》四四所载,一部分由杭州人士消费外,另一部分则贩往各地销售。《宋史》卷一八五《食货志》载淳熙十二年,分拨榷货务乳香于诸路给卖。每及一万贯,输送左藏南库。十五年,以诸路分卖乳香扰民,令止就榷货务招客算请。 又《宋会要·食货》五四云: 同日(绍兴四年七月二十六日),诏:“客人口(算?)请香药等套,欲出外路贩卖者,照引与免出门并沿路商税。如敢夹带不系套内官物者,依匿税法加二等。” 复次,南宋政府又把输入杭州的外货运往沿边的榷场,以与金国贸易。《宋会要·食货》三八云: (隆兴二年)十二月十八日,诏盱眙军依旧建置榷场。于是淮东安抚周淙、知盱眙军胡防言:“绍兴十二年创置榷场,降到本钱十六万五千八百余贯,系以香药杂物等纽计作本。今欲从朝廷斟量支降。……”诏户部先依次支降见钱五万贯,余并从之。 (乾道)九年二月七日,臣僚言:“昨来朝廷曾差使臣般发檀香前去安丰军,同本军知军措置,博易丝绢。今乞将库管檀香依昨来体例般发,委本军措置。”诏于左藏库支给三分以上檀香三十斤,吏部差短使一员管押前去。 (乾道元年)九月十五日,诏光州光山县界中渡市建置榷场。于是知光州郭均申请,“乞从朝廷支降本钱,或用虔布、木棉、象牙、玳瑁等物折计降下。……”从之。 三月十一日,诏随州枣阳县榷场移置于襄阳府邓城镇。……于是权兵部尚书、湖北京西路制置使沈介言:“今于邓城镇修置榷场,欲依旧令总领官司漕臣提领措置;依例支降本钱五万贯,于湖南总领所支拨,令用博易物色;匹帛香药之类,从朝廷支降,付场博易。……”从之。(2)商人对于广州的外货贸易之经营 宋代广州的外货贸易,除如上述,一部分由政府经营外,其另一部分则由商人经营。上节曾说,有好几种由海外输入广州的商品,因为利润很大,除抽解一部分作为关税外,完全由政府及收买,不许商人买卖,以免利人私人之手。这样一来,商人不是不能做这些商品的买卖吗?不是的。上节同时又说,有时因为物品太多,不能全数运往汴梁或杭州,有时因为物品粗重,负担不起运费,政府便将这些外货在广州出卖。因此,商人从政府手中买到这些专卖品(榷货)后,便可自由运往其他地方出售了。复次,在由海外输入广州的许多货物中,政府专卖品不过十种,其余大多数除由政府抽解一部分作关税及收买一部分外,便可在市场上自由买卖。这许多非专卖品的外货的运销,中外商人自然可以经营。所以宋代广州的外货贸易,除一部分由政府经营外,商人更是其中的重要经营者。 苏过《斜川集》卷六《志隐》说广州的犀、象、珠、玉,走于四方。由此可见由广州进口的外货分配于国内各地的普遍。这些外货的分配,有一显著的特点,即分配于当时大消费中心的汴梁与杭州(杭州为大消费中心的理由,见拙著《南宋杭州的消费与外地商品之输入》,《集刊》七本一分),以及沿着各重要交通线而分配于其两旁的都会。现在分述如下。 北宋时代,商人大量的把由广州进口的外货贩人汴梁,因为汴梁在当时是大消费中心,其中住民数量多而购买力强,运销到那里去的商品不愁卖不出去(详见拙著《北宋汴梁的输出入贸易》)。至于贩人汴梁的外货,现可考见的,有如下述: ①香药范成大《桂海虞衡志》说中州人士使用由广州人口的外国沉香石: 中州人士但用广州舶上占城、真腊等(沉水)香。 又《岭外代答》卷七亦云: 顷时(沉水)香价与白金等,故客不贩,而宦游者亦不能多买。中州但用广州舶上蕃香耳。 这里说的“中州”,指的是汴梁一带。又张邦基《墨庄漫录》卷二说外国的各种异香由广州转贩人汴云: 宣和间,宫中重异香:广南笃褥、龙涎、亚悉、金颜、雪香、褐香、软香之类。笃褥有黑白二种……白者每两价值八十千,黑者三十千。外廷得之,以为珍异也。 复次,在广州做官的人,于罢任时,也把香药贩往汴梁出卖。他们虽是官吏,其行径实与商人无异。《宋会要·职官》四四载至道元年六月,诏,“市舶司监官及知州通判等,今后不得收买蕃商杂货及违禁物色。如违,当重置之法”。先是南海官员及经过使臣多请托市舶官,如传语蕃长,所买香药,多亏价值。至是左正言冯拯奏其事,故有是诏。 如《宋史》卷二八七《李昌龄传》说他由广州罢任北返,运载许多药物回汴云: 知广州。广有海舶之饶,昌龄不能以廉自守。淳化二年代还。初(父)运尝典许州,有第在城中。昌龄包苴辎重,悉留贮焉;其至京城,但药物药器而已。 这些官吏既然是那么贪污,他们在广州低价买回的香药绝不是送人或自用,而是在汴梁市场上高价出卖,以便获利。所以孟元老《东京梦华录》卷三说相国寺的瓦市有罢任官员的香药出卖云: 相国寺每月五次开放,万姓交易。……殿后资圣门前,皆书籍、玩好、图画及诸路罢任官员土物、香药之类。 按汴梁人士多半有钱,其消耗香药的数量甚大。《鸡肋编》卷下云: 吴幵正仲云:渠为从官,与数同列往见蔡京,坐于后阁。京谕女童使焚香。久之不至,坐客皆窃怪之。已而报云香满。蔡使卷帘,则见香气自他室而出,霭若云雾,濛濛满座,几不相睹,而无烟火之烈。既归,衣冠芳馥,数日不歇。计非数十两,不能如是之浓也。 又叶绍翁《四朝闻见录》乙集云: 宣政盛时,宫中以河阳花蜡烛无香为恨,遂用龙涎沉脑屑灌蜡烛,列两行数百枝,焰明而香潘,钧天之所无也。 因此我们可以推知,北宋时代,由广州转贩到汴梁的外国香药,一定很多。 ②真珠《宋会要·食货》四一说衢州商人在广州外商处购买真珠,运销人汴云: 景祐四年正月二十七日,衢州客毛英言:“将产业于蕃客处倚富赊真珠三百六十两。到京纳商税院,行人估验价例,称近降诏,禁止庶民不得用真珠耳坠、项珠,市肆贸易不行,只量小估价。缘自卖下真珠,方得限钱,纳税无所从出,乞封回广州,还与蕃客。”诏三司相度,许将真珠折纳税钱。 又同书《食货》四一说真珠由广州进口,经抽解若干作为关税后,准许运往汴梁及四川等地出卖云: (熙宁)七年正月一日,诏定:“诸广南真珠已经抽解,欲指射东京西川贸易者,召有力户三两名委保,赴税务封角印押,给引放行。各限半年,到指射处。与免起发处及沿路税,仍俱(具?)邑(色?)额、等第、数目,先递报所指射处照会。候到日,在京委当职官估价,每贯纳税百钱;在西川委成都知府通判监估,每贯收税二百钱。出限不到,约估在京及西川价,报起发处,据合纳税钱,勒保人代纳。即私贩,及引外带数,或沿路私卖,及卖人各杖一百,许人告,所犯真珠没官,仍三分估一分价钱赏告人。” 又赵扑《赵清献公集》卷二《奏状乞取问王拱辰进纳赃珠》说商人在广州买珠,经长沙贩往汴梁云: 况戢子乔陈状:父舜中元于广州用钱一千余贯,买到上件珠子。只自广至潭(州,即长沙),又入京师,其价已须两倍。 ③倒挂雀朱或《萍洲可谈》卷二说海外的倒挂雀贩人汴梁云: 海南诸国有倒挂雀。尾羽备五色,状似鹦鹉,形小如雀。夜则倒悬其身。畜之者,食以蜜渍粟米甘蔗。不耐寒,至中州辄以寒死。寻常误食其粪亦死。元祐中,始有携至都城者,一雀售钱五十万。东坡《梅词》云,“倒挂绿毛公凤”,盖此鸟也。 按《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卷一四一说《萍洲可谈》作者“朱或之父服……为广州帅,故彧是书多述其父之所见闻,而于广州蕃坊市舶,言之尤详”。而苏东坡之咏倒挂雀,显然因为曾到广东作官,亲眼见过该雀所致。所以这里说海外倒挂雀之贩人汴梁,虽没有明言由哪个海港进口,我们却可以推知是由广州输入的。 到了南宋,由于政治中心的南移,杭州人口增多,成为大消费中心;因此商人多把由广州进口的外货运往杭州出卖。如《宋会要·职官》四四说客商贩运泉、广等地的外货往杭州云: 嘉定六年四月七日,两浙转运司言:“临安市舶务有客人于泉、广蕃名下转买,已经抽解胡椒、降真香、缩砂、苴蔻、藿香等物,给到泉、广市舶司公引,立定限日,指往临安府市舶务住卖。从例系市舶务收索公引,具申本司,委通判主管点检,比照元引色额数目,一同发赴临安府都税务收税放行出卖。如有不同,并引外出剩之数,即照条抽解,将收到钱分隶起发上供。今承指挥:舶船到临安府,不得抽解收税,差人押回有舶船司州军。即未审前项转贩泉、广已经抽解有引物货船只,合与不合抽解收税?”诏令户部,“今后不得出给兴贩南海物货公凭,许回临安府抽解。如有日前已经出给公凭客人到来,并勒赴庆元府住舶。应客人日后欲陈乞往海南州兴贩,止许经庆元府给公凭,申转运司照条施行,自余州军不得出给。其有自泉、广转买到香货等物,许经本路市舶司给引,赴临安府市舶务抽解住卖,即不得将元来船只再贩物货往泉、广州军”。仍令临安府转运司一体禁戢。 这些由广州转贩人杭的外货,多半属于原料性质,由海外输入广州后,一点也没有改变过,便贩往杭州。此外,又有些输入广州的外货,先在广州加工制造,然后运往杭州出售。这可以龙涎香为例。洪迈《夷坚丁志》卷九说在广州加工制造过的龙涎香贩运入杭,致为杭州人士仿制云: 许道寿者,本建康道士,后还为民。居临安太庙前,以鬻香为业;仿广州造龙涎诸香。 又顾文荐《负暄杂录》(《说郛》卷一八)说杭州市肆仿效广州吴氏制造龙涎香云: 龙涎香品……番禺有吴监税菱角香,而不假印脱,手捏而成。当盛夏烈日中,一日而干,亦一时绝品。今好事者家家有之。泉南香不及广香之为妙。都城市肆有詹家香,颇类广香。 按广州吴姓以制龙涎香著名,而买卖又好,故非常有钱。叶氏《爱日斋丛钞》(《说郛》卷一八。《守山阁丛书》本较详细,但昆明旅次,手头无此书,故只好用《说郛》本)云: 有吴氏者,以香业于五羊城中,以龙涎著名。香有定价,日飨如封君。人自叩之,彼不急于售也。 至于广州吴姓制造龙涎香的办法,《岭外代答》卷第八亦有记载: 泡花,南人或名柚花。……气极清芬,与茉莉素馨相逼。番禺人采以蒸香,风味超胜桂林。好事者或为之。其法:以佳沉香薄片劈着净器中,铺半开花与香层层相间,密封之。明日复易,不待花萎香蔫也。花过乃已,香亦成。番禺人吴宅作心字香及琼香,用素馨茉莉,法亦尔。大抵浥取其气,令自薰陶,以入香骨,实未尝以甑釜蒸煮之。[这段记载虽然没有明说是制造龙涎香,但由于其所用原料为素馨茉莉等物,可以推知,因为制龙涎香是要用这些花的:“制龙涎者,无素馨花,多以茉莉代之。郑德素侍其父漕广中,能言广中事,云素馨唯蕃巷种者尤香,恐亦别有法耳。龙涎以得蕃巷花为正云。”(陈善《扪虱新话》卷一五)] 上引各段关于广州龙涎香制造者的记载,《负暄杂录》作“吴监税”,这是就其官名来说;《爱日斋丛钞》作“吴氏”,这是只就其姓来说;《岭外代答》作“吴宅”,这是就其姓名来说:所以三者想同是那一个人。再不然,想同是那一个家族;因为在宋代,好些工商业都是以家族为单位来经营[1],有如中古欧洲的工商业及银行业多由Fuggers及Midici等家族来经营那样。 宋代由广州输入的外货,除运销于汴梁及杭州等大消费中心外,又分配于各重要交通线旁边的都市。上引《赵清献公集》说过,商人由广州贩珠人汴,路过长沙。这想是沿着现今粤汉铁路或其附近的路线走的。由此可知,粤汉铁路,或与它相差不多的路线,在宋代是一条重要交通线。因为交通比较方便的原故,宋代广州的进口外货,沿着这条交通线北上,而分配于其两旁的都市,如南岳市、长沙及鄂州等。范成大《骖鸾录》说广州等地的商品聚集于南岳市云: 八日入南岳。……至岳市,宿衡岳寺。岳市者,环皆市区,江、浙、川、广种货之所聚,生人所须无不有。 又《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一八○说商人由广州贩珠北上,过长沙(潭州)时为当地官吏低价私买云: 先是(任)颛知潭州,会广州大商道死,籍其财,得真珠八十两。以无引漏税,没入官。颛与本路转运判官李章及其僚佐贱市之。 此事又见于《宋史》卷三三○《任颛传》,记载较简,兹从略。又释文莹《湘山野录》卷中亦载此事云: 一岁潭州一巨贾私藏蚌胎,为关吏所搜,尽籍之,皆南海明胎也。在仕者无不垂涎而爱之,太守而下轻其估,悉自售焉。 复次,广药也贩往长沙。《夷坚丙志》卷一九云: 李镛愿应募。西至长沙,见人卖广药于肆。 这里说的“广药”,不见得产于广东,想是来自海外,有如“广香”[2]不出于广东,而来自外国那样。所以在长沙商店中出卖的“广药”,实是出白海外,由广州转贩而来的。此外,广州的商品又运销于鄂州,即现今武汉的前身。范成大《吴船录》卷下说广州等地的货物贩往鄂州出售云: 辛巳……午至鄂渚,泊鹦鹉洲前南市堤下。南市在城外,沿江数万家。廛闭甚盛,列肆如栉,酒垆楼栏尤壮丽,外郡未见其比。盖川、广、荆、襄、淮、浙贸迁之会,货物之至者无不售;且不问多少,一日而尽。其盛壮可知! 上引《骖鸾录》及《吴船录》说贩往南岳市及鄂州的广货,虽没有明说是来自海外,但广州在宋代既是最重要的对外贸易港,其输往内地的商品多半为外货,却是我们可以断言的。 宋代广州的进口外货到达鄂州后,沿着长江西上,便可运往四川。四川一向被称为“天府之国”,在这块肥沃盆地之上的成都非常富庶(见费著《岁华纪丽谱》),所以老远的由广州转贩而来的外货,其价格虽因加上巨额的运费而提高,也不愁没有市场。上引《宋会要·食货》四一熙宁七年正月一日诏,曾说海外真珠在广州进口,为政府抽解若干作为关税后,可以自由运往汴梁及成都两地出卖。从广州珍贵外货的销场上说,成都的地位可以与当时大消费地的汴梁并驾齐驱,其消纳广州珍贵外货的力量之大,可想而知。此外,由广州进口的香药也贩往成都。《夷坚志补》卷二○云: 广州人潘成贩香药如成都,弛担村邸,遇一道人谓曰…… 复次,上一节曾说,政府把在广州收买到的外货运往汴梁,走的是由广东北境过大庾岭以人江西这一条路。到达江西后,如果顺着现今的浙赣铁路向东走,便可往南宋大消费地的杭州。广州的进口外货也沿着这条交通线北上,而分配于其旁边的都市。如《夷坚支甲》卷三说客商把广香贩往浙赣路旁边的贵溪云: 浙西人刘承节自赣州税官回赴调,寓家于赣,但与一子一仆乘马而东。至信之贵溪,牛(?)驻逆旅,逢数贾客携广香同坐。相与问所从来,欲买客香。 此外,因宋代海上交通非常发达,广州的进口外货遂沿着这条海洋的交通线北上,而分配于沿海的都市。杭州便是在海岸附近的一大都市;关于广州进口外货运销到那里去的文献,上边已提及了。复次,广州的进口外货又由海道贩运往明州、苏州、镇江、江宁及密州板桥镇等沿海的都市。张津等《乾道四明志》卷一说广州等地的货物贩往明州云: 南则闽广,东则……商舶往来,物货丰衍……亦东南之要会也。 又上引《宋会要·职官》四四“嘉定六年四月七日”条曾说,贩运广州等地进口外货的商船,须往庆元府(即明州)停泊,以便抽解云: 如有目前已经出给公凭客人到来,并勒赴庆元府住舶。 又朱长文《吴郡图经续记》卷上说广州等地的珍货远物由海道贩往苏州(即吴郡)云: 自朝家承平,总一海内,闽粵之贾,乘风航海,不以为险;故珍货远物,毕集于吴之市。 这里说的“珍货远物”,当然指的是珍异的外货,因为唯有这些外货才够得上“珍”和“远”的称呼。复次,关于广州进口外货之由海道贩往镇江及江宁,《宋会要·食货》五○云: (建炎)三年三月四日,臣僚言:“自来闽、广客船,并海南蕃船,转海至镇江府买卖至多。昨缘西兵作过,并张遇徒党劫掠,商贾畏惧不来。今沿江防拓严谨,別无他虞,远方不知。欲下……广南提举市船(舶?)司,招诱兴贩。至江宁府岸下者,抽解收税,量减分数。非惟商贾盛集,百货阜通,而巨舰衔尾,亦足为防守之势。”从之。 此外,关于广州外货之贩往山东密州板桥镇,《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三四载元丰六年十一月戊午知密州范锷言:“辖下板桥镇隶高密县,正居大海之滨。其人烟市井,交易繁夥,商贾所聚。东则二广福建淮浙之人……络绎往来。然海商至者,类不过数月,即谋还归;而其货物间有未售,则富家大姓往往乘其急,而以贱价买之。……”(《宋会要·职官》四四亦载此事) 又《宋史》卷一八六《食货志》云: 元祐三年,(范)锷等复言,“广南、福建、淮、浙贾人航海贩物至京东、河北、河东等路,运载钱、帛、丝、绵贸易,而象、犀、乳香珍异之物,虽尝禁榷,未免欺隐。若板桥市舶法行,则海外诸物积于府库者必倍于杭、明二州。……”(3)广州的食料贸易(甲)广州的食粮贸易 宋代广州的国内贸易,除外货外,食料的买卖也很大。而广州的食料贸易,尤以米及盐二者为大宗,因为广州在当时是米盐的集散地。兹先述前者。 宋代广东的粮食供给状况,与现在正正相反。现在广东因为食粮的供给少,而人口又多,粮食不足自给,结果每年要从国内米产丰富省份输人大量的米,同时又要从暹罗、安南等产米国家输入大宗洋米。可是广东在宋代因为人口较少,米产虽不及“苏湖熟,天下足”的长江三角洲,却是一个米的输出地方。其出产的米,连同在广西出产的,都先集中于广州,然后运往沿海各地出卖。 两广在北宋时稻的出产已经很好,一年可以收成两次。苏过《斜川集》卷六《志隐》说北宋时两广的农产情形云: 天地之气。冬夏一律。物不凋瘁,生意靡息。冬絺夏葛,稻岁再熟。富者寡求,贫者易足。 当时两广对于农田的开垦,都很积极。如《宋史》卷一七三《食货志》说广东荒田之开辟为农田云: 崇宁中,广南东路转运判官王觉以开辟荒田,几及万顷,诏迁一官。 又《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一九七说广西官吏奖励开垦田亩云: (嘉祐七年七月)甲寅,广西转运使度支员外郎李师中,转运判官都官员外郎刘牧,各罚铜二十斤。先是岭南多旷土,茅菅茂盛,蓄藏瘴毒。师中募民垦田,县置籍,期永无税,以种及三十顷为田正,免科役。于是地稍开辟,瘴毒减息。而师中与牧坐擅除税不以闻,故蒙罚。 因此到了南宋,两广米产更多。 南宋时,两广各地出产的米,除当地消费外,多贩往广州,以便能高价出卖。如《岭外代答》卷四说广西的米贩往广州云: 广西斗米五十钱,谷贱莫甚焉。夫其贱非诚多谷也,正以生齿不蕃,食谷不多耳。田家自给之外,余悉粜去,曾无久远之积。富商以下价籴之,而舳舻衔尾,运之番禺,以罔市利。 这些由两广各地输入广州的米,一部分固为广州住民所消费,但大部分则沿着海洋交通线北上,贩往沿海各地如福建、江、浙等。《宋史》卷四○一《辛弃疾传》说广米贩人福建云: 知福州,兼福建安抚使。弃疾为宪时……谓:“闽中土狭民稠,岁俭则籴于广……” 关于广米之贩往福建,朱熹《朱文公文集》记载更多。如卷二五《与建宁诸司论赈济劄子》云: 广南最系米多去处,常岁商贾转贩,舶交海中。今欲招邀,合从两司多印文榜,发下福州沿海诸县,优立价直,委官收籴,自然辐凑。然后却用溪船,节次津般,前来建宁府交卸。 又卷二七《与林择之书》云: 已累书白帅,宜亟籴广米及台州米。 广中虽云不熟,然亦当胜本(福建)路。 又卷二九《与李彦中帐干论赈济割子》云: 唯有广东船米,可到泉福。 又真德秀《真文忠公文集》卷一五亦说广米贩往福建各地云: 兼福、兴、漳、泉四郡,全靠广米以给民食。(《申尚书省措置收捕海盗》) 又福、泉、兴化三郡,全仰广米以赡军民。贼船在海,米船不至,军民便已乏食,籴价翔贵,公私病之。(《中枢密院乞修沿海军政》) 复次,广州的米也贩往浙江,其中尤以贩往当时大消费地的杭州为多。《宋史》卷三五《孝宗纪》载淳熙九年正月戊子,籴广南米赴行在。 又吴自牧《梦粱录》卷一六说广州等地的米贩往杭州云: 杭州人烟稠密,城内外不下数十万户,百十万口。每日街市食米,除府第官舍宅舍富室及诸司有该俸人外,细民所食,每日城内外不下一二千余石,皆需之铺家。然本州所赖苏、湖、常、秀、淮、广等处客米到来。 又,由广州贩往浙江的米,为浙东销售者亦复不少。朱熹《朱文公文集》卷一三《延和奏劄三》云: 今年旱地广阔,只有湖南、二广及浙西两三郡丰熟,而广东海路至浙东为近。臣昨受命之初,访闻彼处米价大段低平,即尝印榜遣人散于福建、广东两路沿海去处,招邀米客。许其约束税务,不得妄收力胜杂物税钱;到日只依市价出粜,更不裁减;如有不售者,官为依价收籴。自此向后,必多有人兴贩前来。 又同书卷二一《乞禁止遏籴状》云: 缘本路(浙东)两年荐遭水旱,无处收籴,熹今……已……印榜遣人散于浙西、福建、广东沿海去处,招邀客贩。 又同书卷九九《约束籴米及劫掠状》云: (浙东)州县目今米价高贵,止缘早禾旱伤。……兼当司已蒙朝廷给降本钱,及取拨别色官钱,见今广招广南、福建、浙西等处客贩,搬运米斛到来投粜,准备阙米州县搬运前去出粜。 这些由广州贩往浙东的米,多由温州及明州等海港人口,然后分配于浙东各地。同书卷一七《奏梂荒画一事件状》说广州等地的米贩往温州云: 兼闻衢、婺、明州守臣,皆欲丐祠而去;台州亦申本司乞拨钱籴米,数目甚多;又见臣僚劄子,论衢州等处见已乏食,及有指挥行下闽、广劝谕客米前来温州接济:可见一路(浙东)州军荒歉匮乏,事势已急。 至于贩往浙东的广米之由明州人口,记载更多。同书卷一七《奏明州乞给降官会及本司乞再给官会度牒状》云: 臣据明州申:契勘本州今岁阙雨,管下六县皆有旱伤去处。窃虑细民阙食……本州遂于七月十八日具奏,乞支降官会一百贯,下本州循环充本,雇备人船出海,往潮广丰熟州军收籴米斛,准备赈籴账济。 又同书卷二一《与宰执劄子》云: 乞且拨十四万三千石先付熹前去,将绍兴府诸县一例作逐日籴济外,所乞余数,却乞纽计价钱,付熹前去与知明州谢直阁同共措置雇,募海船,收籴广米,接续籴济。 又同书卷二六《上宰相书》说两广的米贩往明州,然后分配于浙东各地云: 又以连日不雨,旱势复作,绍兴诸邑,仰水高田,已尽龟坼;而山乡更有种不及入土之处;明婺台州,皆来告旱,势甚可忧。……而荒政之中,有两事焉,又其甚急而不可少缓者也。一曰,给降缗钱,广籴米斛。今二广之米,舻舳相接于四明之境,乘时收籴,不至甚贵,而又颗粒匀净,不杂糠枇,干燥坚硕,可以久藏。欲望明公察此事理,特与敷奏,降给缗钱三二百万,付熹收籴,则百万之粟,旬月可办,储蓄既多,缓急足用,政使朝廷别有支拨一纸,朝驰而米夕发矣……二曰…… 又朱熹《朱文公别集》卷五《(与)林子方(书)》亦云: 所部皆以旱告,盖去岁之灾所不及处,无不病者。而衢婺荐凶,公私匮竭,尤未知所以为计。独念贵境犹可告籴,已请于朝降本收籴,且散膀自广以东诸州,以招诱之矣。恐番禺以西更有出米通贩去处,谨复具公移,并以膀文三百道,仰累颐指,散下晓谕,不胜幸甚。此米得到四明,尚须搬运,方得至衢婺,正自不易为力。鼠伎已穷,日夕忧惧,高时有可以见教者,深所欲闻。 此外,《宝庆四明志》卷四亦说广州的米贩往明州云: 明之谷……一岁之入,非不足以赡一邦之民也。而大家多闭籴。小民率多仰米浙东、浙西,歉则上下皇皇。劝分之令,不行州郡。至取米于广以救荒。 至于两广的米之贩往江南东路(约略相当于现在的江苏)及浙西(杭州除外),因当地是著名的产米之区,而距离广州又较远,自较贩往福建及浙东等地为少;不过当收成不好,食粮少而价贵的时候,广州的米也运销到那里去。《宋会要·食货》五九载隆兴二年九月四日,知镇江府方滋言……其后方滋又言:“今岁江东二浙皆是灾伤去处,独湖南、广南、江西稍熟。相去既远,客贩亦难,势当有以诱之。欲乞朝廷多出文榜,疾速行下湖、广诸路州军,告谕客人:如搬贩米斛至灾伤州县出粜,仰具数目经所属陈乞,并依赏格,即与推恩。……”从之。 又同书《食货》四一载淳熙七年十月十七日,大理正兼权吏部郎官马大同言,“被旨差措置拘催江东转运司和籴米斛,今条具下项:一,江东(转)运司籴米本钱内,度牒五百道,恐期限既迫,难以变转。凶荒之年,犹仰客舟兴贩二广及浙西米前来出粜。今岁二广更旱,浙西米价亦自顿长,窃恐将来本路必至大段阙食。……” 这里要注意的是:南宋时两广的米为什么要由广州转贩往福建及浙江等地?我们知道,米是重量体积较大而价值又较贱的商品,在以前因负担不起较重的运费,很少运到远地出卖——由海道运往更是少有。可是到了南宋,情形却大大不同。在这时,福建浙江一带是人口密集区域,至于两广则是人口稀薄地带。据《宋史》(卷八八至九○)《地理志》,这几个地方在南宋初年人口的分布,约如下表: 就各地人口分布的稠密来看,闽、浙等地对于食粮的需要当然远较两广为大。不特如此,福建及浙江人口虽然很多(即对食粮的需要大),食粮的供给状况却不见得很好。福建多半都是山地,肥美的农田甚少,故食粮出产有限,不足自给。《宋史》卷八九《地理志》云: 福建路……土地迫陿,生籍繁夥,虽硗确之地,耕耨殆尽,亩直浸贵,故多田讼。 又方勺《泊宅编》卷中云: 七闽地狭瘠而水源浅远。其人虽至勤俭,而所以为生之具,比他处终无有甚富者。垦山垄为田,层起如阶级然。…… 又《真文忠公文集》亦云: 福与兴、泉土产素薄,虽当上熟,仅及半年。专仰南北之商转贩以给。(卷一五《奏乞拨平江百万仓米赈粜福建四州状》) 福之为州,土狭人稠。岁虽大熟,食且不足。田或两收,号再有秋,其实甚薄,不如一获。(卷四○《福州劝农文》) 至于浙江,其农田虽不至如福建那么硗瘠,但大部分人口多赖工商业及政治为生,从事农业者少,再加以人口太多,故食粮出产亦不能自给。《宋史》卷八八《地理志》说浙江人民多以工商为业云: 两浙路……人性柔慧……善进取,急图利,而奇技之巧出焉。余杭、四明,通蕃互市,珠贝外国之物,颇充于中藏云。 又《咸淳临安志》卷五六载陈密学(襄)《劝学文》亦说杭州一带人士多以工商为业云: 杭东南之会藩也,其山川清丽,人物秀颖,宜有美才生于其间;然自建学以来,弦歌之声萧然,士之卓然有称于时者盖鲜,反不迨于支郡,何也?岂非濒海之民,罕传圣人之学,习俗浮薄,趋利而逐末,顾虽有良子弟,或沦于工商释老之业,曾不知师儒之道尊,而仁义之术胜也? 而且杭州又是当时政治中心,在那里及其附近自然有不少靠政治过活的居民。浙江既然有这许多人靠工商业及政治为生,其从事农业的人民自然很少,从而食粮的供给状况自然不会很好。反观两广,稻田既可一岁再熟,人口又比较稀少,情形正正相反。这么一来,在闽、浙一方面是对食粮的需要大,对食粮的供给少,粮价自然高涨;在两广一方面是对食粮的需要小,(有如上引《岭外代答》卷四所说,“以生齿不蕃,食谷不多”)对食粮的供给多,粮价自然低跌。如蔡绦《铁围山丛谈》卷六说广西博白米价的低廉云: 博白有远村号绿红,皆高山大水,人足迹所勿及。斗米一二钱,盖山险不可出。 这固然是一个很极端的例子;不过如上引《岭外代答》卷四所载,广西斗米也不过是五十钱而已。这与当时浙江的米价比较(尤其是有旱灾时),真有天渊之别。如《朱文公文集》卷一七《奏衢州官吏擅支常平义仓米状》云: 今来旱势已成,衢州尤甚。昨日有转运司差出官员自彼回来,说城中米价已是七十文足一升。 两地米价的差额既是这么大,所以商人把两广的米运往闽浙一带出卖,虽然要负担相当的运费(由于那时海上交通的发达,运费当可较前大减),仍可获利。因此,不用等到元代,米已成为海上运输的主要商品;而广州在宋代除了是外货的集散地外,同时又是一大米市,有如现在的芜湖那样。(乙)广州的食盐贸易 宋代广州的食料贸易,除谷米外,盐的买卖也很大。广东沿海一带是盐的大生产地。在沿海出产的盐,先集中于广州、潮州、惠州及南恩州等地,然后运销于其他地方;其中尤以广州的买卖为大。《宋会要·食货》二六载绍兴二年十一月十四日,提举广南东路茶盐公事管因可言,“本路产盐:广州盐仓每年课利三十万贯以上;潮州十万贯以上;惠州五万贯以上;南恩州三万贯以上。除广州已有盐官外,三州久例止是本州官兼监……”。 由沿海集中于广州的盐,沿着各条交通线而分配于广东、广西的一部,以及江西、湖南两省的南部。《宋史》卷一八三《食货志》说广州的盐贩往两广各地云: 广州、东筅、靖康等十三场,岁鬻二万四千余石,以给本路及西路之昭桂州,江南之南安军。 又《宋会要·食货》二六亦载绍兴三年九月十八日,广南东西路宣谕明橐言,“二广比年以来,盐货通流,其价倍增,自合随时措置。窃见广东西路转运司每岁于广州都盐仓,或于廉州、石康县盐场,支拨各路诸州郡岁额盐。诸路州郡各差衙前来搬取所受之数。其盐,朝廷累降指挥,增添价钱。每斤至官收价钱四十七文足。每箩计一百斤,收钱四贯七十文足。广东如南雄等州官卖实价每箩至十千,广州亦自至八九千……。” 其中关于广州的盐之贩往广东北部,《宋史》卷三二八《蔡挺传》亦云: 番禺岁运盐英、韶,道远多侵窃杂恶。(蔡抗)命十舸为一运,择摄官主之。岁终会其殿最,增十五万缗。 关于广州的盐之贩往广西,《宋史》卷三八六《范成大传》亦载广州盐商请勿由广西政府专卖,以便运盐前往出卖云: 知静江府。广西窘匮,专藉盐利,漕司尽取之。……成大入境……数年,广州盐商上书,乞复令客贩。宰相可其说;成大出银钱助之。人多以为非。下有司议,卒不易成大说。 复次,广州的盐又贩往江西南部虔州及南安军等地。在北宋初年,政府要专卖盐,把淮盐运到这些地方出卖。可是,因为办理不善,运费太重,盐质恶劣而价又昂贵,当地人民乃食用由广州转贩而来的物美价廉的私盐。《宋史》卷一八二《食货志》云: 熙宁……三年,提点刑狱张颉言:“虔州官盐卤湿杂恶,轻不及斤,而价至四十七钱。岭南盗贩入虔,以斤半当一斤,纯白不杂,卖钱二十。以故虔人尽食岭南盐。”(又见于《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三一三) 江西则虔州地接广南。……虔盐不善……民多盗贩广南盐以射利。(又见于《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一九六) 及元丰三年,政府遂依照蹇周辅的提议,遣人贩运广盐于江西虔州及南安军等地。《宋史》卷一八二《食货志》云: 元丰三年,(章)惇既参政:有郏直者……迎合惇意……乞运广盐于江西,即遣蹇周辅往江西相度。周辅承望惇意,奏言:“虔州运路险远,淮盐至者不能多,人苦淡食。广东盐不得辄通,盗贩公行。淮盐官以九钱致一斤。若运广盐,尽会其费,减淮盐一钱,而其盐更善,运路无阻。请罢运淮盐,通搬广盐一千斤于江西虔州南安军,复均淮盐六百一十万斤于洪、吉、筠、袁、抚、临江、建昌、兴国军,以补旧额。”诏周辅立法以闻。周辅具盐法并总目条上。……遂以周辅遥领提举江西广东盐事,即司农寺置局。(《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三——有相似的记载) 此外,广州的盐又贩往湖南南部出卖。湖南本是淮盐的销售区域,但北宋初年,商人即已私运广州廉价的盐至该地出卖,以便获利。《宋会要·食货》二三载开宝四年四月,广南转运使王明言:“本道无盐禁,许商人贩鬻。兼广州盐价甚贱,虑私贩至荆湖诸州,侵夺课利,望行条约。”诏自今诸州并禁之。 到了元丰年间,乃因蹇周辅的提议,由政府贩运广盐到湖南南部出售。《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三四八云: 初蹇周辅言,“韶、连、郴、道州,可以通广盐敷百万,代淮盐食湖南”。故奉议郎郏亶亦乞运广东盐往湖南路郴、全、道三州。诏送(提举荆、湖南路常平等事张)士澄,(转运判官陈)傯等相度。至是(元丰七年九月己酉)奏上,乃下监司行之。(《宋史》卷一八二《食货志》有相似的记载) 又《宋史》卷三二九《蹇周辅传》亦云: 先是湖南例食淮盐。周辅始请运广盐数百万石,分鬻郴、全、道州……法既行,遂领于度支。四、结论 综括上述,可知宋代广州的国内外贸易都很发达。其贸易的商品,因为广州在当时是主要的对外贸易港的原故,以由南洋各国贩人的真珠、犀角、象牙及各种香药为多。这些外货输入广州后,复由政府及中外商人分别经营,沿着各主要交通线而运销于国内各都市,尤其是汴梁、杭州以及成都等大消费中心。复次,又分别由汴梁、杭州贩往辽、夏、金等国。 除外货以外,米及盐等食料也是宋代广州贸易的主要商品。在两广各地出产的米,先集中于广州,然后由海道贩往当时人口密集而农产又少的福建及浙江等地;故广州在当时实是一大米市,有如现今的芜湖那样。复次,在广东沿海出产的盐,亦先输入广州,然后运销于两广各地,以及江西、湖南的南部。 因此,宋代的广州实赖屯贩贸易(Transittrade,或曰通过贸易)来维持。它一方面是海外各国与国内各地贸易的居间者,把外货输入,分配于国内各地;同时,又把在两广各地出产的食料转贩往沿海各省及湘赣等地。 固然,工业品的制造也能养活宋代广州人口的一部分;如输往海外的洪钟、铜瓦等工业品,及运销于国内的龙涎香,是在广州制造的。但这不过是少数而已,大部分的出口工业品,如金银器、丝织品、漆器及瓷器等,在当时并没有产于广州的记载,想是先在国内各工业生产地制造,然后经由广州贩往海外的。预览时标签不可点收录于话题#个上一篇下一篇 |
转载请注明地址:http://www.hulubaa.com/hlbzz/9967.html
- 上一篇文章: 国药准字益生菌第三终端市场的最后一座
- 下一篇文章: 年08月309月1日保健食品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