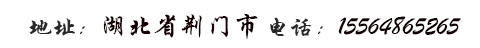细读金瓶梅040西门庆上任,葫芦官判
|
诗曰: 赌近盗兮奸近杀,自古及今不曾差。 奸赌两般都不染,太平无事好人家。 话说西门庆新开了家绒线铺,又新搭上一个伙计,这人也不是个守本分的,姓韩名道国,字希尧,本是破落户韩光头之子。 如今家道中衰,他便接了老爹的差使,在郓王府做校尉,在县东街牛皮小巷居住着。此人爱慕虚荣,喜欢吹牛皮,死的能说成活的。许人钱,如捉影捕风;骗人财,如探囊取物。 自从做了西门庆的伙计,这绒线铺里的东西就像他家的一样,一上来便新做了几件光鲜衣裳,成天穿着,在街上撸着袖子恨不得横着走。 人们看到,便将他的配字“韩希尧”叫做“韩一摇”了。 韩道国的老婆是屠夫王屠的妹子,因在家中排行老六,所以都叫她王六儿。又生的长挑身材,长着一张紫膛色的瓜子脸,约莫二十八九岁的样子。两口子育有一女,一家三口过活。 韩道国还有一个兄弟,名字叫啥不知道,因排行居二,所以都叫他韩二了。他还有一个浑名叫二捣鬼,是个赌钱的小混混,在外头另住着。 韩二与嫂子王六儿有一腿,经常趁着他哥哥不在家、特别是在铺子里住宿不回家的时候,他便跑来与嫂子一起喝酒,到了晚上就给哥哥戴绿色帽子了。 要知道天下没有不透风的墙。 原来街坊上有几个浪荡子弟,见王六儿搽脂抹粉的,又打扮得妖里妖气,经常站在门口卖弄风骚,便前来挑逗。 可王六儿呢,又装始作假正经,嘴巴又臭又硬的,张口便骂人。 这其中有几个小伙子被骂惨了,对她心生不满,发现他与小叔子不三不四后,便暗中结成群,一起商量要整她一顿。 韩道国这房子有门面三间,左右两边都是邻居,屋后子便是逆水塘。 这帮人采好点,有时夜晚扒在墙上偷看,有时白天暗使小孩子在后塘谎说捉虫子,单等韩二过来好捉奸。 有一天,韩二打听到他哥不在家,便大白天过来与嫂子一块儿喝酒,结果喝醉后倒插上门,在屋子里鬼混。 不料想这一切都被那帮浪荡子弟跟踪到,叫潜伏在后塘的一个小孩子从门槛底下爬进去,然后把后门门栓打开,众人一齐涌进屋里来。 韩二想夺门逃跑,却被一拳打倒在地,几个混混七手八脚地给绑了。 韩六儿还在炕上,慌忙中穿衣不迭。 一人进去,先把裤子夺在手里,将二人都一条绳子拴出来游街。 不多会儿,便围了一群看热闹的人,走到牛皮街厢铺停下,那整条街巷都轰动了。这一个来问,那一个来瞧的。 这其中有一位老头见这对男女被绑在一起,就问左右看热闹的人:“这是怎么一回事儿?” 旁边有多嘴的对老头说:“你老人家还看不出来吗?这是小叔偷嫂子。” 那老头点了点头儿说道:“可恶,原来小叔子奸嫂子,要是送到官府,叔嫂通奸,两个都得绞死。” 那旁边多嘴的人认得这老头,是有名的老色鬼,绰号叫作“陶扒灰”,一连娶三个儿媳妇,都被他扒了,因此就插嘴对他说:“你老人家深谙条律,一口断定这小叔养嫂子的是绞罪,若是公公养儿媳妇的要论什么罪呀?” 老头一听便知道是在揭他的短,红着脸低着头,灰溜溜地走了。这正是: 各人自扫檐前雪,莫管他人屋上霜。 再说那天韩道国在铺子里忙完,并没有住在店铺里,打烊后便往家里赶。 时值八月中旬,他身上穿着一套儿轻纱软绢衣服,又新买的一顶帽子,便在大街上炫耀起来,走路都带拉风的。 可今儿他感觉街上的人有点反常:见到自己后,或坐或立,口若悬河,滔滔不绝,走得远了,又在后头指指戳戳的。 正纳闷的时候,遇上两个熟人,一个是开纸铺的张好问,一个是开银铺的白汝晃,韩道国见了,便连忙上前作揖施礼。 张好问说:“韩老兄多日不见,听说在西门大官人府上高就,开宝铺做买卖,我等缺礼失贺,休怪休怪呀!”又让他进铺子里坐下。 那韩道国也不客气,扯过凳上便坐,二郎腿一翘,把脸仰着,一边摇着扇子,一边洋洋得意地说:“学生不才,全靠沾上各位的光,我与恩主西门大官人做伙计,赚钱三七开。掌巨万之财,督数处之铺,大官人还须敬我几分哩!俺可不是普通打工者哟。” 白汝晃插嘴说:“可俺听说老兄在他门下只管线铺生意哩。这又是怎么回事儿?” 韩道国笑着说:“两位有所不知,线铺生意只是名头而已。他府上大小买卖,出入资金,哪些不经过我的手?大官人对我言听计从,有福同享,要是我离开一会都不行。大官人每天从衙门中回来,第一件事儿便是请我去陪侍他吃饭,没我便吃不下饭去。俺们俩在他那小书房里,闲中吃果子拉家常,经常是坐到半夜。” 白汝晃说:“照你这么说,大官人对你不错喽!” 韩道国接着说:“可不是嘛!昨儿他家大夫人过生日,在家中摆酒请客,他夫人首先请的我,喝到二更天才回来哩。彼此通家,再无忌惮。说来两位可能不信,就是他个人的私生活,也常跟我说哩。学生我可是一个行止端庄,一丝不苟,对工作兢兢业业,在钱财上公私分明,与财取之有道。就是傅自新也怕我几分。不是我自夸,大官人最信任的人是我。” 正说在兴头上,忽见一人慌慌张张地跑过来对他喊:“韩大哥,你怎么还有空在这坐着?叫我一阵子好找。”说着把他拉到偏僻处,这才跟他说:“你家出事了,大嫂与二哥被街坊在床上逮着了,拴到铺里,明早还要送去见官哩。你还不早早托人情,处理此事?” 韩道国一听,犹如晴天霹雳。口中只咂嘴,气的直跺脚便要走。却被张好问过来扯住,说到:“韩老兄,话还没说完,怎么这么着急要走?” 韩道国连忙甩开,只说:“大官人有要紧事找我商量,恕我失陪了。”慌忙而去。这正是: 谁人挽得西江水,难洗今朝一面羞。 韩道国跑到家中一打听,才知老婆与兄弟韩二被人捉奸拴在铺子里去了,又慌忙返回绒线铺子来,与来保商量怎么办。 来保说:“这事儿只要去找应二叔,叫他出面对县中李老爹说情,不论多大事情都能摆平。” 这韩道国二话不说,直奔应伯爵家。应婆娘派丫头出来回复:“不在家,不知去哪里了。有可能在西门大老爹家。” 韩道国说:“我就是从那边来的,不在西门府里。”又问应宝呢,回复说也跟着一块走的。 韩道国慌了爪子,又来清河县红灯区勾栏院里来找。 原来应伯爵被湖州何蛮子的兄弟何二蛮子,号何两峰的请去,正在四条巷内何金蝉儿家喝酒呢。 韩道国见了,就像见了菩萨一般,请他出来说话。 应伯爵喝的满脸通红,帽檐上插着剔牙棒儿。 韩道国唱了喏,拉到僻静处,如此这般说了一通。 应伯爵说:“你既然找到我了,我怎么能不帮这个忙呢。”于是辞别了何两峰,与韩道国一同回家,将前因后果问个清楚。 韩道国说完便一个劲儿哭求:“此事若是闹到县衙便没法收拾了,还望二叔去大官府衙上说说,讨个帖儿,转呈李老爹,一定不能叫你侄媳妇送官呀。事后必重谢二叔。”说着便跪下磕头。 应伯爵一把拉起他说:“贤契,你摊上这档子事,我岂能不帮?你快写个帖儿,把一切闲话都丢开,只说你经常不在家,娘子被这伙光棍时常打砖掠瓦,欺负骚扰。你兄弟韩二一时气不过,与他们理论,反被这伙人围住,拳打脚踢的,一同拴在铺里了。望大官府发个帖儿,跟李老爹说明。” 韩道国听罢忙取来笔砚,写了说帖,放在袖子里。 应伯爵领着他一起来到西门府门口,问守门的平安儿:“你爹在不在家?” 平安说:“爹在花园书房里。二爹和韩大叔请进来吧。” 二人进来花园,有画童儿小厮在那里扫地,看到他们进来便引至书房,说到:“二位先请坐。俺爹刚才去后边了。我这就过去请爹来!” 说罢,画童儿便来后边潘金莲房里找西门庆,看到春梅便问:“春梅姐,爹在这里吗?” 春梅骂道:“贼种,真活见鬼了!爹何曾沾过俺家门槛儿?明明在隔壁六娘房里,偏偏跑来俺屋里问!” 画童又转身往李瓶儿屋子这边走来,看到绣春在石台基上坐着,便问:“爹可在你们那屋子?应二爹和韩大叔来了,在书房里等爹说话哩。” 绣春说:“爹在里头,看着娘给哥裁衣服哩。” 原来西门庆拿出几匹布料,一匹大红纻丝,一匹鹦哥绿潞绸,叫李瓶儿替小官哥裁毛衫、披袄、背心、护顶之类的。 炕上铺着大红毡条,李瓶儿正在忙裁剪,奶妈抱着官哥儿,迎春呢,执着熨斗。 绣春进来,悄悄推了迎春一把,迎春就说:“你推我干什么?要是撒了这火掉在毡条上怎么办。” 李瓶儿也问:“你推她做什么?” 绣春说:“画童过来了,说应二爹来了,请爹过去说话哩。” 李瓶儿说:“小奴才儿,应二爹来了,你直说就是了,却推她干啥?” 西门庆听了,便对站在门口的画童说:“先叫你二爹坐会儿,我马上就去。”然后直等到衣服裁完才过来书房见应伯爵二人。 二人起身给他作揖,西门庆招呼二人坐下。应伯爵对韩道国使眼色,然后说道:“韩大哥,你有什么话,尽管对你大官府说。” 西门庆也说:“你有什么事,不妨直说。” 韩道国便一五一十说了,正说到“街坊有伙不知姓名棍徒……”时,被应伯爵打住,然后说:“贤侄,你不妨长话短说。噙着骨头露着肉,也不是个事儿。对着你家大官府在这里,就直说吧:韩大哥常在铺子里歇宿,家里没人,只有他娘子一人,还有个女孩儿。左右街坊,有几个不三不四的,见男人不在家,时常过来骚扰。欺负得急了,他令弟韩二哥看不下去了,家来骂他们几句,反被这伙光棍不由分说,围上来打个臭死。如今二人被拴在铺里,明要还要送去本县李大人那里去。他哭哭啼啼,托我来对哥说个情,讨个帖儿,对李大人说明,卖个人情。有了他令弟也是一般,只不要他令正出官就是了。”又说:“你把那说帖儿拿出来与大官人瞧瞧,好派人替你送过去。” 韩道国连忙从袖中取出,又双膝跪下,说道:“小人忝在老爹门下,万乞老爹看在应二叔份上,照顾一下,举家没齿难忘。” 西门庆一把拉起,说道:“你请起来。”又展开帖儿观看,只见上面写着:“犯妇王氏,乞青目免提。” 西门庆说:“这帖子不能这么写!只提你令弟韩二一人就行了。”又向应伯爵说:“与其我拿帖去给县衙说,不如叫地方到时改了报单,明儿交由我提刑院来审理了。” 应伯爵说:“好好!如此就更好办了!”又对韩道国说:“韩大哥,你还不给恩老爹下个礼儿?” 韩道国便倒身磕头如捣蒜。 西门庆叫来玳安,吩咐他:“你外边快叫个衙役的班头来。”不一会,叫了个穿青衣的衙役来,在旁边伺候。 西门庆叫到跟前,吩咐:“你先去牛皮街韩伙计的住处,问问是哪牌哪铺,人被关在什么地方,然后对那保甲说,就称是我的钧语,叫他们把王氏立刻给我放了。再查查那几个光棍的名字来,改了报帖,明早解提到提刑院,送我衙门里听审。”那衙役应诺,领命出门。 应伯爵说:“韩大哥,你也同衙役一道去,忙你的事去吧!我还要和大官人说会话儿。” 那韩道国千恩万谢地出了门,与衙役一起回牛皮街处理家务事了。 西门庆陪伯爵在翡翠轩坐下,又叫玳安放桌儿:“你去对你大娘说,昨日砖厂刘公公送的木樨荷花酒,打开筛来,我与应二叔要喝酒,顺便把糟鲥鱼蒸了端来。” 应伯爵说:“我还没来得及谢哥,昨儿承蒙哥送了两条好鲫鱼。俺回去送了一条给家兄,只剩下一条,对房下说,拿刀儿劈开,送了一段与小女,其他的都打成窄窄的块儿,将它用红糟儿培着,再搅些香油,安放在一个磁罐里,留我一早一晚地就饭吃,或者赶上有客人来,蒸上一碟儿来吃,也不枉辜负了哥哥的盛情。” 西门庆听了,点了点头,又告诉他这鱼的来头:“刘太监有个兄弟叫刘百户,因在河下管芦苇场,赚了几两银子,又在五里店新买了一所庄子,却拿皇木来盖房子,近日被我衙门里办事官查到,缉拿到案了。依着夏提刑,要先罚一百两银子,还要押送他到省院审理。刘太监一见便慌了,亲自送来一百两银子到我这里,再三央求,想把大事化小小事化了。不瞒你说,咱家做着些生意,日子也能过得去,谁希罕他这点钱?何况刘太监平日里与我交情也不错,时常受他些礼,今儿不能因这些事情,不给面子吧?我是分文不取,只叫他将房屋连夜拆了。到衙门里,只打了他家人刘三二十下,这事就算过去了。事情办妥,刘太监过意不去,宰了一头猪,送我一坛自造荷花酒,两包糟鲥鱼,重四十斤,又两匹妆花织金缎子,亲自登门来谢。彼此脸上都有光,也算交个情分。” 应伯爵听罢,便说:“哥哥不说,俺也知道你是对钱无感的人。可那夏大人行伍出身,两手空空的,他不捞些儿,拿什么过日子?哥哥,你自从到任以来,可曾与他一起审理几桩案子?” 西门庆说:“大小也问了几件公事。别的倒也罢了,只是他贪婪成性,有些事不分青红皂白,见了钱便放人,这成何体统?我有时看不惯,便与他理论,‘你我虽是个武职官儿,掌管这刑条,还放些体面才好。’”说罢,叫下人端来酒菜。 西门庆用小金菊花杯倒满荷花酒,陪着应伯爵喝起来。 再说那伙人,见青衣衙役来到地方,把妇人王六二放回家去,又拘了总甲,查了各人名字,明早押送提刑院审理,众人见状都面面相觑,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 有人说韩道国是西门庆家的伙计,西门庆又是提刑院的二当家,若是押解到提刑院审理,恐怕这事要弄砸了。 韩道国这边又送了衙役五钱银子,衙役便屁颠屁颠地叫保甲查出那几个人名字,送回西门庆府,专等次日早上押解。 到了第二天一大早,西门庆与夏提刑两位官,老早在衙门里坐厅等着。不多时,地方保甲带上人来,头一个便是韩二,跪在前头。 夏提刑看着报单喊:“牛皮街一牌四铺总甲萧成,为地方喧闹事……”又见上头第一个叫韩二,第二个车淡,第三个管世宽,第四个游守,第三个郝贤。都叫上来,逐一花名对了一遍。然后先问韩二:“你为什么被送过来?” 韩二却恶人先告状说:“小人的哥哥韩道国是个买卖人,经常不在家住,小男幼女的,被街坊这几个光棍白天胡搅蛮缠,夜晚又来砸门,百般欺负。小的在外另住,来哥哥家中看到,一时气不过,便骂了几句。谁知这伙棍徒不由分说,将俺揪倒在地,拳打脚踢,还被绑来送到老爷案下。望老爷明查。” 夏提刑又问那几个混混:“你们几个怎么说?” 那伙人一齐告道:“老爷休听他胡言乱语!他就是赌钱的韩二捣鬼。他哥哥不在家时,便与他嫂子王氏有奸。那王氏平日里放刁耍赖骂街,泼皮淫妇一个。昨儿他两又在一处鬼混,被小的们逮个正着,还有衣服为证。” 夏提刑又问地方保甲萧成:“那王氏怎么不见送来?” 萧成怎么好意思说被衙役放了呢?只好说:“王氏脚小,怕行动不便,没来。” 韩二忙在下边,两眼一劲儿给西门庆递眼色。 西门庆好久才欠身对夏提刑说:“长官,此事也无需审问那王氏了。定是王氏有些姿色,这帮光棍前来调戏她不遂,才设计的这个圈套。”又叫那为首的车淡上来,问道:“你们在哪里捉住的韩二?” 众人说:“昨儿在他哥哥屋里捉到的。” 西门庆又问韩二:“王氏是你什么人?” 保甲替他回:“是他嫂子儿。” 西门庆又问保甲:“这伙人从哪里进屋子里去的?” 保甲说:“越墙进去的。” 西门庆听罢大怒,骂道:“我就说你们这帮光棍不干好事儿!他既是小叔子,王氏也是有服之亲,难道不许他上门走动?再看看你们这帮光棍,又是他家什么人?为何敢越墙进去?何况她男人不在家,又有幼女在房中,你们如此这般非奸即盗了。” 西门庆说罢,喝令左右拿夹棍来,每人夹上二十大棍,只夹的皮开肉绽,鲜血淋漓。 这几人都是少年子弟,出娘胎以来何曾受过这苦头,一个个被夹的号哭动天,呻吟满地。 这西门庆也不等夏提刑开口,便下令:“将韩二拎出去在外听候。把这四个都给我拿下收监,取供画押后送问州府。” 这四人被押到监中后,个个心怀鬼胎,互相埋怨起来,后又吵个不停。 监中人又吓唬他们几个说:“你四个若是被送问,都是徒罪。到了外府州县,都是九死一生。” 这帮人一听便慌了,等家人来狱中送饭的时便捎口信回家:叫各人父兄花钱,抓紧上下打点托人情。 这其中还有托人找到夏提刑的,夏提刑便说:“这王氏的丈夫是你西门老爹门下的伙计。他在中间扭着要送问,同僚之间,我不便插话。还须得托别人跟他说去。” 也有托吴大舅出来说情的。 四家父兄托了一圈人情,发现都不好使,便都慌了,会在一处。都知道西门庆家不差钱,也不敢前来打点。其中有一个说:“吴千户那边俺找了几遍,就是不依。又听人说,在东街上住的开绸绢铺应大哥兄弟应二,和大官人关系不错。咱们不如凑几十两银子,送给应二,叫他替咱们说个情,可能管用。”于是以车淡的父亲开酒店的车老儿带头,每人拿来十两银子,一共凑齐四十两银子,一齐送到应伯爵家,央求他出面来说情。 应伯爵收下银两,便将众人打发走了。他娘子便说:“你既先替韩伙计出力,摆布这伙人,为何又揽下这银子,反替他们说起情来,这不叫韩伙计报怨?” 应伯爵说:“我能不知道这事儿?我自有办法的。”又把银子兑了十五两,包放袖中,直奔西门府而来。西门庆还未回来。 (未完待续, |
转载请注明地址:http://www.hulubaa.com/hlbjb/11917.html
- 上一篇文章: 花生,是糖尿病的加速器吗医生保护胰岛
- 下一篇文章: 美食香辛料卤煮家庭厨房调料大全集成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