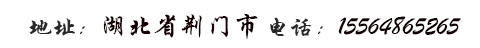张治ldquo围城rdquol
|
北京治白癜风最好的医院是哪家 https://baike.baidu.com/item/%E5%8C%97%E4%BA%AC%E4%B8%AD%E7%A7%91%E7%99%BD%E7%99%9C%E9%A3%8E%E5%8C%BB%E9%99%A2/9728824?fr=aladdin ◎作家与作品◎ 内 容 提 要 自年归国至年,钱锺书与外在环境的身心接触和忧患感发绝非通常人们所想象得那么隔阂。在寻求如何表现这十年多来切中时代脉搏文学抒怀与学术思考的过程中,他将历代无数中外文豪作为他书斋生涯的“患难知己”,而且其中最具有代表意义的,就是两部荷马史诗《伊利亚特》与《奥德赛》。借助于若干文本细节的考索与钩沉,通过从《钱锺书手稿集》建立的个人阅读史线索,将有可能展现钱锺书对于荷马史诗里“围城”“回乡”两大主题传统的独特体认,以及在个人文学活动中不断通过戏仿和隐喻对这两个传统做出的回应与争胜。这不仅有助于理解钱锺书个人家国心怀的曲折表达,也可以由此呈现中国现代文学在世界文学潮流中的某种同源性和同步性。 关键词 钱锺书荷马阅读史战争文学 年夏,钱锺书一家归国,坐法国客货船“阿多士II”号的三等舱,从马赛到上海。钱锺书在香港独自先下船,经海防赴云南昆明,至西南联合大学报到。到学校后,因战事开学延后至11月,便在10月间回上海省亲,与家人小聚数日。随后返回昆明,开始了他的教书生涯。据当时学生回忆,钱锺书在西南联合大学外国语文学系执教,除了开设“文艺复兴时代文学”“现代小说”和大一大二的英文课,还在多名教授合开的课上讲授了荷马的两部史诗。1这门合开课程,回忆者称之为“欧洲文学名著选读”,所言上课时间为“年暑假后”,这与钱锺书年7月间离职的情况存在矛盾。而根据清华大学档案保存的“国立西南联合大学必修选修学程表”,—学年,外文系就已有一门“本系教授”开设的“欧洲名著”课,一个学年(未分学期)八个学分。2假如是当时听课学生事后回忆的那样,九位教授总共讲了十部著作(“荷马史诗”算作一部),那么一个专题大概接近一个学分,就相当于“文艺复兴时代文学”这种一学期两个学分课程大概一半的工作量了,绝不是一两次讲座就完结的规模。由此可知:大概是在年11月至年初,钱锺书在西南联大讲授过几次《伊利亚特》与《奥德赛》。回国就登上最高学府的教授讲席,开讲便是荷马史诗,他一定早有充足的阅读准备。 虽然说讲授“欧洲名著”从荷马史诗开始是顺理成章的,但此时钱锺书选择这个题目或接受这个部分的教学任务,不能说是一种偶然。方从西方人文学术中心(牛津、巴黎)归国,作为欧洲文化重要源头的荷马史诗,最早涉及战争中的人类命运与情感、回归家园与漫游世界种种关系,这切中当时陷入苦难与危机的整个文明世界所面对的问题。而对钱锺书来说,他讲读荷马史诗的经历和感受,也渗入他面对时局世事的种种心绪之中,同时会以改头换面的修辞方式运用在他的文学创作和学术著述文字里。通过已刊著述及近年影印出版的读书笔记来追踪钱锺书的思想轨迹,会发现从当初回国后初登课堂就开始讲授荷马史诗,直到写成“忧患之书”《谈艺录》和“中国现代文学中最有趣和最用心经营的小说”《围城》,这十年间围绕着家国心事与个人际遇,有始终贯彻下来的两条主题线索,“围城”和“回乡”,或隐或显,代表着钱锺书这时期的独特思考。“围城”是钱锺书小说标题,也是全书之心眼,有关其背后的种种出典,涉及中西古今若干种作品,其丰富性不能凿实为《伊利亚特》的特洛伊“围城”战争意象。3而“回乡”散见于钱锺书诗文著述之间,有哲理思考、诗性隐喻等多个层次,的确可找出对奥德修斯漫游精神的阐述传统,但历代文家与哲人的发挥又未必都需要归于《奥德赛》的直接影响。然而向来文学才思上特具禀赋之人,对于他所倾慕的典范和榜样总是既有效仿之实,又不免有争胜之意,往往不肯自道渊源。在此不妨将刚留学归来的钱锺书在西南联大外文系讲授的荷马史诗课程,看作他此后十年文学生涯的一个界碑。 一 虽然我们在《钱锺书手稿集》里找不出一篇读《伊利亚特》或《奥德赛》的笔记,《谈艺录》几次提及荷马之名也基本都是转述近人意见,但钱锺书对于荷马史诗的文本细节一直有“信手拈来”的熟稔:作为著作预备稿的《容安馆札记》里经常出现的荷马引文,用的是哈佛大学“娄卜古典丛书”本;《管锥编》提及荷马有十次以上:《奥德赛》四次、《伊利亚特》三次;还有一次提及残本小史诗《马尔吉忒斯》(Margites,传为荷马所作)里的著名比喻,用“娄卜”旧版《赫西俄德与荷马风作品集》;其他则是所引近人批评言论里道及荷马者。还有一处《伊利亚特》用的是蒲伯(AlexanderPope,—)译文。根据钱锺书的阅读习惯,那些能经常运用却又不见于读书笔记的经典著作,往往都是读过多遍、烂熟于心的。兹有一例可以说明钱锺书对此西方诗家之祖的深切领会,即《通感》一文提及“荷马那句使一切翻译者搔首搁笔的诗”4,指《伊利亚特》第3章第、行,形容几个特洛伊长老无力参战,高坐城门之上发表演说,好像是深林中的知了,发出“百合般的声音”: τεττ?γεσσιν?οικ?τε?ο?τεκαθ?ληνδενδρ???φεζ?μενοι?παλειρι?εσσαν?ε?σι· 校勘者或认为“百合”这里原词有误,当另有它义。但假定文字上没错,理解也不难,而且具有独特的文学效果。罗念生、王焕生合译本译作“很像森林深处爬在树上的知了,发出百合花似的悠扬高亢的歌声”。而钱锺书体会荷马诗句的“通感”妙处,认为这是把高处鸣蝉声音传到树下的过程比作百合(或铃兰)的形态,更为精彩地传达效果。因此他译作: 像知了坐在森林中一棵树上, 倾泻下百合花也似的声音。 原文中的?ημι一字,就是“使之垂流”“倾泻”的意思,这与《礼记·乐记》里所谓“上如抗下如队”的“队”(坠)之修辞相互发明。罗王译文增出一个无关紧要且先后矛盾的形容词“悠扬高亢的”,反而完全没理会原话里视觉、听觉的移位之妙。 根据当事人的回忆,钱锺书在西南联大的课堂上是全程英语讲授的。他讲课时不太提问,连贯的内容里屡有引人入胜之处。吴宓在日记中曾提到借阅李赋宁“文艺复兴时代文学”和“现代小说”两课的听讲笔记,表示非常佩服。然而,关于荷马史诗的课,却没多少学生或同事提到过,只有后来翻译《红与黑》的赵瑞蕻以极为抒情的方式描述过听课感受: 荷马史诗是那样神奇和浩瀚:我曾谛听沿长街弹唱漫步的,那个盲诗人的七弦琴音,追随着他永生的诗行,跌落在那个小亚细亚不幸的王国的宫墙边;或者想象当年一个金苹果竟闯下那一场涂炭生灵十年的战祸,那个希腊绝代佳人海伦能有多大的魅力使天下英雄,同声齐起,执干戈而效命沙场?而奥德修斯浮沉海浪二十年的漂泊生涯,在我的心灵上引起浪漫的遐想,飘过鲛妖动人的歌声,食莲实人的奇异的影子。5 这主要涉及两部史诗里的一些著名场景和情节,包括荷马的身份和史诗早期的流传方式、特洛伊围城战争的缘起以及中西文学里都出现过的“红颜祸水”题材。说“浮沉海浪二十年”显然是把特洛伊十年战争也算进来的“浪漫的遐想”,《围城》里的方鸿渐都早就将《奥德赛》题名译作“十年归”了。“鲛妖”指的是用歌声诱惑水手们的塞壬女妖(Sirens),晋张华《博物志》卷二中说过“南海外有鲛人,水居如鱼,不废织绩,其眼能泣珠”(又见于干宝《搜神记》),唐李颀有《鲛人歌》。以此典化译荷马史诗中的海妖,也许就是钱锺书课堂上的发挥。“食莲实人”对应的是英译本常用的“lotus-eaters”一词,原文希腊语作λωτοφ?γοι6;其中的lotus,凡人吃后忘记一切烦恼,便不想回家,具体所指并不确定,可能是某种枣类。7 名物究竟何指不必多言,可以感受到这“食莲实人”扮演的角色主要在于以魔法食物使得远游的贵客忘记回家。“回家”(ν?στο?),是开篇诸神对英雄们所许诺的结局,也是全诗的主题。“当他们一吃了这种甜美的洛托斯花,就不想回来报告消息,也不想归返,只希望留在那里同洛托法戈伊人一起,享受洛托斯花,完全忘却回家乡。”(王焕生译文)就此而言,歌声能诱海上舟子堕海的“鲛妖”,其魔力也有同样的一种效果,即忘记“回家”,如希腊教父作家亚历山大里亚的克莱芒就认为塞壬歌声乃是世俗享乐诱惑的象征8,然而贪于享受忘忧花果的是奥德修斯的伙伴,经受塞壬歌声诱惑的却是他本人,只因为捆绑在桅杆上而得以逃生。罗马帝国时期爱卖弄自己学问的提比略皇帝时而会向学者们提问:塞壬女妖通常所歌为何物?9我们今天看到的《奥德赛》里显然是有答案的,正如西塞罗在《论至善与至恶》中所记:常常吸引来往航行者的不是她们的甜美声音,亦非她们新颖丰富的诗歌,而是她们提供的知识:如果爱智慧的人爱知识胜过爱自己的家,那么像奥德修斯一样想追随塞壬入海也就毫不奇怪了。10 钱锺书在课堂上提到荷马史诗中这些魔幻事物,并非仅要引起某种浪漫的遐想。他对英雄回家故事中坎坷遭遇的留意,与他不久前漫长的归航感受不无关系。这段旅程自晚清以来都差别不大11,都是从马赛经意大利至埃及北部,穿过苏伊士运河,出红海,自亚丁湾经印度洋北部至斯里兰卡,穿过马六甲海峡至新加坡,经停西贡(今胡志明市),到香港,再至上海。地中海的一段海上之旅(也正是《围城》小说开场前的部分),与荷马史诗里的航海世界多有交叠之处。《后汉书·西域传》里甘英听闻“安息西界船人”所说“海中善使人思土恋慕,数有死亡者”,遂打消了渡海的念头。“思土恋慕”的意思尚不太明确,《晋书·四夷列传》则将“船人”的话记录为“海中有思慕之物,往者莫不悲怀,若汉使不恋父母妻子者,可入”。轮船上的钱锺书自然会记得这个故事。12不须今天学者撰文指出汉籍里“思慕之物”便是地中海东岸所流传的塞壬女妖之古希腊神话13,钱锺书未尝不会如此联想。 《围城》里时常出现荷马史诗的影子,作者会拈出《奥德赛》中某个奇妙魔幻的经历,放入他的文字之中。除了听课学生印象深刻的“鲛妖”与“食莲实人”,在《围城》第五章开头——整部小说恰好过了一半的时候,钱锺书使用过《奥德赛》第十卷里的一个典故: 上海这地方比得上希腊神话里的魔女岛,好好一个人来了就会变成畜生。 显然是指旧太阳神的女儿、女法师喀尔刻(Circe)。奥德修斯的伙伴们因为吃了喀尔刻的宴席,都变成了猪。在赫尔墨斯的帮助下,奥德修斯没有变形,用武力逼迫喀尔刻就范,把伙伴们重新变回成人。但是,喀尔刻仍然以语言的魔法困住了奥德修斯,她使奥德修斯和同伴们每日享用美酒佳肴,生活了一年之久。 钱锺书此时还读了古希腊“神秘宗”大师普罗提诺《九章集》的法文译本。14普罗提诺引过一句《伊利亚特》:“让我们坐船逃往挚爱的父邦”15,继而说“正如奥德修斯逃离传说中的魔女喀尔刻和卡吕普索”;此后又言“他们为实在的处所感到愉悦,就像长期漂泊在外的游子,回归自己安乐平和的家园”16。卡吕普索(Calypso)也是《奥德赛》中的角色,她是提坦神的后裔,奥德修斯漫长的回乡之旅,在她的海岛上耽搁得最久,长达七年。虽然卡吕普索对奥德修斯满是爱意,许诺他永生,但奥林波斯诸神终因后者“一心渴望能望见故乡升起的缥缈炊烟,哪怕以死为代价”(I58—59)的祈愿而感动,遂命卡吕普索改变主意。古希腊语中,卡吕普索一名出自动词καλ?πτω,意即“遮掩”“包裹”“欺骗”,赫西俄德《神谱》称她是“非常诱人的卡吕普索”17,虽然直接危害性并不大,但是从阻碍奥德修斯回乡的功能上看,却和喀尔刻同样都是最难摆脱和克服的。 由此观之,塞壬女妖、“食洛陀斯人”、魔女喀尔刻和卡吕普索是不同层次上诱惑回乡途中的奥德修斯,使其产生“思慕”的神秘事物。钱锺书回国之初,选择讲授荷马史诗里的《奥德赛》一书,引发其兴致的源头也许就在于对“回国”/“回家”这一主题的理解,而最能深化这一主题、使得回家之旅变得艰难而充满挑战意义的情节,便是以上这些“海中思慕之物”。 钱锺书在《札记》中 |
转载请注明地址:http://www.hulubaa.com/hlbcs/9068.html
- 上一篇文章: 柑橘黄龙病苹果蠹蛾马铃薯甲虫梨火疫
- 下一篇文章: 百年风华middot诗映初心南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