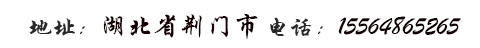我与狸奴不出门
|
1 今天是公元年6月1日,上海解封的第一天,儿童节。这个儿童节,来得措手不及,让已经习惯“不出门”的我毫无准备。而我能想到送给孩子的礼物,是继续陪孩子在诗词里长大。 记得小时候,爸妈的卧室里有个小小的书柜;还不识字的我,喜欢翻看《上下五千年》、《一千零一夜》书中的图画,幻想古人的故事;便一识字,我更是流连在那方寸之间,有《唐诗三百首》、有《红楼梦》,还有一本破旧的薄薄的蓝皮的《诗词格律》。 就像陆游儿时随手翻开藤椅上的一本陶渊明诗集,便被其中一句“暮作归云宅,朝为飞鸟堂”击中,仿佛陡然推开了一扇亮窗。我也一样,一个懵然无知的孩子,被这些一知半解的文字所吸引。真是少年不识愁滋味,打小便莫名有了一份“小舟从此逝,江海寄余生”的恬淡诗情。平平仄仄平平仄,仄仄平平仄仄平。正是伴着嘈嘈切切的声律起伏,完成了一个男孩最初的人生启蒙。 时隔多年,我还时常感到自己是何其幸运;一个调皮的孩子是怎么发现、并且愿意依偎在这个冷清的角落呢。诗词和文学除了感动自己,也让我在少年时期就收获了五位同好的友谊。30年前,我们因文学结缘,30年后,我们成了人生挚友,虽分隔天涯,彼此间还保留着难得的纯粹。这份纯粹,在诗里、在歌里、也在每一次“云喝酒”的日常。所谓相知半生,归来仍是少年。 诗词曾带给我的滋养,我也试着用它来“喂养”孩子。在家教贝拉诗词,虽经年不辍,但也有颇多周折难处。不是每个孩子都能进入这个冷清的角落,贝拉也曾将诗词课业当成一个负担,继而反抗、时而罢课,用尽萝卜大棒也是枉然。我一直在想,为何孩子和我不一样,难道诗词本身还不足以拉扯他们吗。 直到某天,我重读了《十一月四日风雨大作二首》。 2 八百多年前的一天,中国农历十一月四日,南宋朝绍熙三年冬。除了北方的金人建成一座石桥(后世的网红桥卢沟桥)和南方州县下了一场暴雨之外,与往常并无二样。 一位68岁的老人正躲在屋内,听外面风雨大作。他提笔写道,“风卷江湖雨暗村,四山声作海涛翻”。有一丝凉意,他往炉内添了一把木柴,狸奴也凑了过来。老人哈了口气,继续写道,“溪柴火软蛮毡暖,我与狸奴不出门”。就这样,他和小家伙在家里窝了一整日。 那天晚上,老人做了一个梦,然后反反复复睡不着。他坐起身、又拿起笔。他说自己“僵卧孤村”是有些悲哀,但不是为了老身短长;他想起刚刚做的那个梦,梦里依然冷风吹雨,而自己却是一身戎装,披盔甲、佩长枪、胯下一只大号的狸奴,戍守在早已沦陷的边关轮台。“夜阑卧听风吹雨,铁马冰河入梦来。”写毕,收笔,黯然,神伤。 这位老人,就是陆游。年少起便轻狂不拘,放浪形骸,自号放翁。7年前,他规劝朝廷奉行节俭、以资养战,收复中原失地,结果遭小人弹劾,皇上遂以“嘲弄风月”为由,赐他告老还乡。他把自家宅院改名“风月轩”,聊以自嘲。 陆游信奉写诗是一种修炼,诗作经常无题,或是随手写上某年某月某日作几首。他说自己“六十年间万首诗”,写诗是他的日常。后来还真有人统计过,他是作品存世最多的诗人;更有甚者,一位研究中国南宋经济史的学者,苦于缺少素材,便把《陆游诗全集》当作一手史料。 说回那天,屋外风雨大作;白天,因为怕冷,他和猫猫没有出门;梦中,他化身千里之外,处处金戈铁马。同一日,他写下《十一月四日风雨大作二首》。 千年以后,人们记住了,冰河铁马的清秋大梦。却很快忘了,老人与狸奴的可爱日常。 3 重读陆游的那天,偶然翻到《陆游传》的附录年表。 某页。绍兴十四年,陆游二十岁,居山阴。应试落第。夏秋间娶唐琬。新婚宴尔,曾赋《菊枕诗》,惜不传。 又一页。绍兴十六年,陆游二十二岁,居山阴。受母所迫与唐琬离婚,约在本年。 又几页。绍兴二十五年,陆游三十一岁,居山阴。春日出游,于沈园遇唐琬,赋《钗头凤》。词云“春如旧,人空瘦,泪痕红浥鲛绡透。桃花落,闲池阁。山盟虽在,锦书难托。莫、莫、莫!” 又几页。绍熙三年,陆游六十八岁。九月,居山阴奉祠,四十年后重游沈园,而园已易主,唐婉已故去多年,墙壁早已藤蔓斑驳,当年上面的题词被人转刻入石,读来伤怀,怅然作《禹迹寺南有沈氏小园》。诗云“坏壁醉题尘漠漠,断云幽梦事茫茫;年来妄念消除尽,回向禅龛一炷香!” 又几页。庆元五年,陆游七十五岁,居山阴。春,三游沈园,赋《沈园》二首。诗云“城上斜阳画角哀⑵,沈园非复旧池台;伤心桥下春波绿,曾是惊鸿照影来。” 又几页。开禧元年,陆游八十一岁,居山阴。十二月二日夜,梦游沈园,起赋《十二月二日夜梦游沈氏园亭两首》。诗云“路近城南已怕行,沈家园里更伤情。”“城南小陌又逢春,只见梅花不见人。” 又几页。嘉定元年,陆游八十四岁,居山阴。春,陆游再游沈园,赋《春游》。诗云“沈家园里花如锦,半是当年识放翁。”这园子的花儿,多半都认得我了吧。 还是那些曾经熟谂的句子,却不再是支离的典故片断。老人的一生年表,也不再是六位皇帝和十一个年号轮替的注角。这个寺南的沈园,串起了老人几十年的挂念。以前模糊的人物身影,便有了真切的血肉形态,活脱在我眼前。在老人的心头案边,一直存放着他一次次回去、一次次梦见的小园一角。白居易说,身与心俱病,容将力共衰;老来多健忘,唯不忘相思。一语中的。 又翻回绍熙三年,那页还明白写着“十一月,奉敕再任冲佑;作《十一月四日风雨大作二首》”。 我找来完整的两首原作。这是我生平第一次把这两首诗放在一起来读、当作一首诗来读。 以前读诗,或能感到诗中文辞气势,进而体查诗人的良苦用心。这次读诗,却发现了诗与诗之间的筋骨纠缠。冠着同样标题的两首诗,一首家乡,一首远方;一首平常,一首沧茫。 在诗词的世界里,或许泾渭分明;而一个人的内心,却无法分清,何为拯救、又何为逍遥。 4 这哪是一个人的悲哀。在陆游身后,我分明看见,他和他那个时代苦难文人的重重叠影。读陆游的《十一月四日》,又分明是在读辛弃疾的《破算子》;读“夜阑卧听风吹雨”,你读到“醉里挑灯看剑”;读“铁马冰河入梦来”,你读到“梦回吹角连营”;读“尚思为国戍轮台”,你读到“了却君王天下事”;读“僵卧孤村不自哀”,你读到“可怜白发生”,甚至一种“休将白发唱黄鸡”的倔强。 这是诗与诗之间的唱和,是诗人与诗人之间的呼应。这个回响不只在所谓“赢得生前身后名”,也在乎生存际遇的往来流长。 陆游年表继续写道,“嘉泰三年,辛弃疾起知绍兴府兼浙东安抚使。秋,辛弃疾欲为陆游筑舍,辞谢而止。”说的是辛弃疾去绍兴赴任,听说陆游正赋闲在家,贸然登门拜访;当他发现陆游住得实在太差,便执意为他重修旧屋,被陆游谢绝。 年表中没写的是,这次相遇是两位的第一次见面,是在陆游写作《十一月四日》的十年以后。那年陆游78岁,辛弃疾63岁。陆游婉拒辛弃疾美意的同时,写下一首《草堂》作为答谢。 诗云“幸有湖边旧草堂,敢烦地主筑林塘”,即使草堂破败“漉残醅瓮”“风紧春寒”,亦可“插遍野梅纱帽香”,借着酒劲在纱帽上插满梅花,还请小友“浩歌陌上君无怪”,只因我本“世谱推原自楚狂”。 时光仿佛回到三十年前,诗人还在蜀中任职,他在杜甫草堂边上开辟了一处菜园,亲自躬身耕种,寻常劳作。《草堂》虽不似《茅屋为秋风所破歌》那般雄浑辽阔,但都是诗人们从日常中辟出的生活一角,我们才得以一窥诗人内心的高远宁静。正所谓“竹杖芒鞋轻胜马,谁怕?一蓑烟雨任平生”。如此而已。 也正是在这样的故事里,在这样的人情中,我们看到了不一样的诗词画面。诗不在远方,诗在眼前,诗在日常,甚至诗在苟且。 也许,等我把这些融入到骨血之后,才能把它们化作一篇篇日记,一个个生活叙事;才能让孩子摸得到唐诗的边、碰得到宋词的角,让她觉得这些古早悠长的文字,不再陌生遥远,而是一千零一个故事,是排队换班的幻想朋友,站在跟前。 于是,一年前,我开始了新的一次远足探寻。挖掘诗人的故事,编排诗词里的日常。把诗词按着生活场景拆开了、揉碎了,分成不同的场景和主题。 5 每周只讲一个主题。 我会讲“托人带话”。讲《逢入京使》“马上相逢无纸笔,凭君传语报平安”,讲《折花逢驿使》“江南无所有,聊赠一枝春”,讲《芙蓉楼送辛渐》“洛阳亲友如相问,一片冰心在玉壶”。 我会讲“老家来人了”。讲“来日绮窗前,寒梅著花未?”讲“近乡情更怯,不敢问来人”,讲“对酒两不饮,停觞泪盈巾”, 我会讲“劝酒诗”的风格迥异。讲白居易劝酒,是“晚来天欲雪,能饮一杯无?喝一个?”,讲王之涣劝酒,是“今日暂同芳菊酒,明朝应作断蓬飞。时间不早了,喝吧。”讲李白劝酒,是“人生得意须尽欢,莫使金樽空对月,喝!古来圣贤多寂寞,唯有饮者留其名。喝!五花马、千金裘,呼儿将出换美酒,与尔同销万古愁。喝喝喝!” 直到有一天,贝拉开始问我,为什么诗人都是爷爷呢?我便找来李清照、顾太清这样的奶奶天团。贝拉又问,为什么奶奶们只写词、不写诗呀。我便找来秋瑾讲《秋海棠》,“平生不借春光力,几度开来斗晚风”,告诉她谁说女子不如男。 后来,贝拉喜欢听凯叔讲李白的故事,她说要给李白做一个盲盒手办,一身长衫白衣,站在一条船上;我挑刺说,李白不是“天子呼来不上船”嘛;她会反驳说,李白上的是自己的船,故事里说李白是在船上喝酒、捞水里的月亮掉下去的,当然得上船了;哦对了,我得给李白挂一个酒葫芦。 贝拉在学“送别”时,提出了质疑。她说,爸爸,上次你讲劝酒诗,说“劝君更进一杯酒,西出阳关无故人”,这次你又说“莫愁前路无知己,天下谁人不识君”,后来到底有没有朋友啊。 再后来,我也给贝拉讲中国历史、讲铁马冰河,我给每一段历史故事配上一首定场诗。我讲亡国,会对贝拉说,同样是亡国、做亡国奴,你看这人跟人有多大的不同啊。有的勿宁死、“至今思项羽,不肯过江东”,有的悲愤、“十四万人齐解甲,更无一个是男儿”,有的悔恨、“小楼昨夜有东风,故国不堪回首月明中”,有的平常度日、“商女不知亡国恨,隔江犹唱后庭花”,更有的一享贪欢、“此间乐,不思蜀”。 讲着讲着,贝拉妈也参与了进来,成了贝拉的同学、我的助教,和孩子一起享受诗词之美。即使在疫情期间、足不出户的日子,我们家也是其乐融融。 最后我想感谢诗词,感谢诗人和他们的故事。我希望,把“我与狸奴不出门”送给孩子的日常,把“铁马冰河入梦来”送给孩子的志向。陪更多的孩子,在诗词里长大,保留内心的一份淳良。 (图片取自网络) |
转载请注明地址:http://www.hulubaa.com/hlbzz/11454.html
- 上一篇文章: 民间故事书生访友夜归,入荒村遇美寡妇,想
- 下一篇文章: 没有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