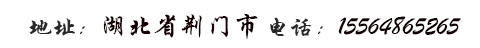故事相公落榜后性情大变,还当街对我动手,
|
北京青春痘哪个医院好 http://m.39.net/disease/a_9120700.html 本篇内容为虚构故事,如有雷同实属巧合。 引子 北京城里有条棋盘街,棋盘街上有个闻冤铺。 铺主人,名胡说,字八道,号妄言居士。生来重瞳,多智近妖,可闻枉死之冤,可断难解之案。 1 胡说从苏府走出来,垂着头,神色不明。 苏府公子苏澈失踪,他受托寻人,最终却查得苏澈已被害,而两名倾世花魁,一个锒铛入狱,一个香消玉殒,叫人好不唏嘘。 胡说今日特意登门致歉,将所受礼金悉数退还,思忖一番,终是不忍心如实相告,只叹息了一句,“苏少爷已得真自在,不必再寻。” 他说得隐晦,苏老爷却像是依稀有了感应,怔坐良久,怆然落下泪来。这个位高权重的两朝泰斗,像是一瞬间便苍老了许多,垂暮如风前残烛。 胡说只觉心中怅然,如鲠在喉,久久无言,只埋首走路。 一辆马车辚辚行来,前有斥候呼喝开路,行人纷纷避让两边。 楠木车身,金漆雕饰,饰以璎珞美玉,华贵又雅致。窗牖被一帘淡蓝色的绉纱遮挡,纱面用朱线细细勾描着一朵欲放的菡萏。一枚银制的令牌悬于车檐下,上刻有“怡亲王府”四字,随着马车的走动,轻轻撞击着壁沿。 这样规格的仪仗,再加上这枚令牌,京中百姓一望便知,是怡亲王府辛夷郡主的车舆。 胡说蓦然愣住,一只脚迈出去一半,身形却像是被施了咒似的,牢牢地定在了路中央。 “王府出行,闲人避退!” 斥候策马高呼,尘土四舞。扬起的马蹄转瞬便到了胡说的眼前。他竟也不避让,像是发了魔怔,一瞬不瞬地直盯着马车。 “眼瞎啦,快让开,喂,说你呢!”斥候不耐烦地驱赶道,说话间一扬手,马鞭便凌空抽了下去! 一声裂帛,手指粗细的马鞭结结实实地落在了胡说身上,衣袖登时炸开了破口,露出胳臂上一道血痕。 “住手!” 忽然有人清声喝到。车夫勒停了马车,一只柔荑素手探出,掀开了绉纱。 斥候顿时变了脸色,赶忙跳下马,诚惶诚恐地跪倒。 没有人注意到,在这一瞬间,胡说飞快地移开了目光,垂下眸子,默然站到一边。 绉纱后露出的是一张年轻女子的面庞。只着淡淡的粉黛,清丽如出水之莲。云鬓泼墨,仅用一支通体晶莹的玉簪挽着,周身再不见其他饰物,单从装扮上来看,倒不像是贵族女眷。只是眉目间的气度,又远非寻常女儿能比。 “参见郡主!”斥候恭敬地回禀,“前方受阻,不得已惊动了郡主,小人该死!” 辛夷朝前一望,见一名灰袍男子低头站在路边,身上鞭痕赫然,不由得微微蹙起了眉,“此道拥堵,你绕别的路走就是,我已吩咐不可扰民,你怎地还动了手?” 她平心静气,声音并不大,却自带着一种不可侵犯的冷冽之感。斥候匍匐在地,迭声告饶,“小人知错,请郡主息怒!” 辛夷没有过多追究,只淡淡道:“向人好生赔礼。”说罢,她又看了一眼路边的男子,见他背着身,将头埋得很低,自始至终不曾抬起,想来是畏惧王府威严,便也不再说什么,放下帘子,重坐回车内。 马车复又行进,车轮辘辘,驶过长街。 胡说束手让到路边,始终低着头,肩背微微塌着,瘦削的身形显出一种寥落。直到马车走远,即将没入街尾,他方才无声无息地抬眼望去。 十七不在身侧,谁也看不懂他眼里的意味。 2 “下人是毛躁了些,郡主何必与他们计较?”车内还坐了一名老妇,慈眉善目地劝慰道,斟了一杯水递上。 辛夷冲她笑了笑,接过瓷杯,抿了几口,手指习惯性地抵住额头。 “哎呀,可是头又疼了?”老妇急忙凑过来,替她轻轻揉着太阳穴,神色满是关切,“郡主可要当心自己的身子。这一日日地不得安眠,长久下去,铁打的身子也都熬虚了。我看,还是奏请老爷,再传御医来瞧瞧吧。” “嬷嬷不用担心。”辛夷却轻轻摇头,温言道:“御医都瞧过那么多次了,连章院使都说没有根治的法子,只让将养着。左右也不是什么要紧的毛病,就不必再劳师动众了。” 她轻声细语,却态度坚决。白嬷嬷只得暗自叹息,心中更生爱怜。 自三年前那场变故后,辛夷郡主就得了心悸失眠的病症,夜夜梦魇,睡不安稳,常枯坐着,便是一整宿。性子也冷淡了下来,郁郁寡欢,少见笑颜。 白嬷嬷忽地想起什么,“说到这个,我听说城里有家香料铺,近来名声大噪,因其售有一种名叫‘浮生’的熏香,静气安神,最是助眠。不少贵人家都趸批了,咱们要不也去买一点试试,说不准真的有用。” 老人柔软的手指揉捏着穴位,辛夷觉得头痛缓和了大半,一松弛,倦意席卷,身体倚上车壁,微阖双目,轻声道:“试试也可。听嬷嬷的。” 白嬷嬷应下,隔着锦帘吩咐了几句,让车夫转向去往香铺。 3 十七见到负伤回来的胡说,差点没跳起来。扬手扔了酒壶,抢身上来,先是提溜着胡说上上下下检查了好几遍,稍稍松了口气,又问是被谁所伤,言辞间森冷的杀气已漫上了眉宇,就等胡说吐出一个罪魁祸首的名字,他就要一跃而起找人算账。 可饶是他怎么追问,胡说只沉默不语,一副失魂落魄的模样。 见他这般,十七突然就有了猜测,犹豫半晌,小心翼翼地开口,“遇着她了?” 胡说好半天才轻轻一颔首。 额。十七霎时无言,讪讪地收起了袖中已经呼之欲出的“欲眠”剑,摸了摸鼻子,愣是想不到该说什么。 辛夷郡主随王妃去京郊灵谷寺礼佛,行斋半年,两个月前方才回京。自打知道她回来的消息,胡说便无事不出门,躲着官道走,甚至跑去城郊桃花坞参加什么天下第一大会,都不过是为了能避则避。 然而,北京城就这么大,不期而遇的一天,总会来。 纵使相逢应不识,十七很难去想象胡说眼下的心情,只是悄悄叹口气。 屋外忽然传来一阵喧嚣。十七正处在这种相对无言的尴尬中,闻声赶紧做出一副好奇的样子,顺势看向外面。 一男一女正在拉扯,看架势是一对夫妻,年岁都不算大。男人醉醺醺的,摇摇晃晃地走着,手上拖着一个女人,骂骂咧咧:“老子让你去打酒,你倒跑个没影。背着我在外面偷人,你当我不知道?我今天倒要看看,你勾搭上了哪个小白脸!走!” 那女人被他钳住手,跌跌撞撞地跟着,鬓发散乱,额头已青紫了一大块,衣襟也被扯得歪斜,狼狈不已,一直低声下气地解释着,男人却充耳不闻,嘴中不干不净地谩骂,手上也没轻没重,几乎是将女人拉扯着在地上拖行。 围观的人群交头接耳地议论着,却是见怪不怪。 “这刘润生又在打老婆了。” “看他那样子,大白天的,就烂醉如泥。不是喝酒,就是赌钱,也没个正经营生,真看不出来以前还是个秀才。” “考了好多年都不中,自暴自弃了呗。祖上传下来的那点家底,估计也快要被败光了。” “真是可惜了他老婆柳氏,跟了这么个混账玩意儿。” “哎,听说两个人以前也是恩爱的,只是好景不长,刘润生屡次落榜后就性情大变,喏,成了如今模样。” “喔唷,你瞧瞧那脸,如花似玉的,姓刘的也真能下得去手。” “你倒是怜香惜玉,该不会和她有什么……嘿嘿嘿。” “呸,胡说什么,叫你嫂子听见,不得扒了我的皮!” 看客窃窃私语,讨论得热火朝天,却无一人上前劝阻。毕竟是家务事,外人总归是不好僭越干预。 柳氏戚戚哀求:“我没有,我只是去城中买东西——” 刘润生见她还敢辩解,酒气冲脑,抬手就是一个巴掌甩了过去。柳氏像是一根被折断的芦苇,身子横着摔了出去,整个人伏倒在地,半天起不来身。一个小小的纸包裹从她怀中掉落。 刘润生也愣了片刻,却见周围人群指指点点,尽是看他笑话的模样,怒气便又难以遏制地冲上来,伸手拽住柳氏的胳膊,要将她强行拽走。 “啊!”一声惨呼。 刘润生的手被人在半空中捉住,反向一扭,登时脱了臼。 来人是一名青衣男子,身法快得出奇,只单手擒住刘润生,随随便便地扣着,便叫他动弹不得。 “打女人?能耐啊。”青衣男子冷冷讥诮,手腕运力,刘润生满头的冷汗涔涔而下,手臂已经被扭转到了极限,痛得大呼小叫。 “十七老板高抬贵手。”旁边有人出来劝道:“这两口子,床头吵架床尾和嘛。” 十七冷哼一声,见刘润生浑身颤抖,几乎快要晕厥过去,这才松手甩开。 刘润生忌惮地看了他一眼,不敢说什么,只狠狠啐了一口,兀自走开。 柳氏将小纸包捡起揣好,急忙爬起,匆匆朝十七福了福身,快步追上了刘润生的背影,并不敢靠前,只怯生生地跟在后面。 看完热闹,围观人群作鸟兽散。其中一人颇为忿忿不平,咂咂嘴,小声念叨着。 “这刘润生真是作孽哦,合该被老天爷收了!” 4 那位嘴碎的看客,约莫是给嘴巴开过光,竟一语成谶。 当天晚上,城西一户人家走水,待邻里合力将火扑灭后,赫然在二楼的卧房里发现了个人,面目依稀可辨,正是刘润生。 好事不出门,坏事传千里,翌日下午,连个囫囵日尚未过去,这起惨烈的事故就已经在城中百姓口里传了好几回合,说得是绘声绘色,不遗巨细。 “要我说啊,人在做,天在看,恶事做多了,夜路总会撞见鬼。看看那刘润生,一个大活人,竟在自个儿家中被烧死了。” “合该他倒霉!听说,他从赌坊回来路上,一个更夫还瞧见了他,酒气熏天的。更夫眼见他进了家门,不一会,又听他骂了几句,上了二楼。那会功夫,人还好好的。哪知更夫才走过一条街,大火就“噌”地蹿了起来。” “火是怎么起的?” “说出来啊,都怕你不信!那刘润生醉得不省人事,失手打翻了烛台,灯油洒了出来,连着床榻整个烧着了。他却仍是无知无觉,倒头大睡,竟就在睡梦中生生被浓烟闷死了!” 听的那人嘬起了嘴,倒吸了一口气,又问道:“官府已经定案为意外了?” “那不然呢?更夫的证词,证实了刘润生是独自回家的,左右邻居也不曾听到争执,府衙看了现场,也没有找到他人纵火的痕迹。” “哎,那刘润生的老婆呢?” “要不怎么说,是老天爷收了他呢。他老婆当晚去酒铺打酒,因为先前赊账未结,和酒铺老板求了老半天,才给打了半壶酒回去。到了家,便只见一屋的废墟和丈夫了!你可是没听见柳氏的哭声——”说的那人顿了顿,夹了一筷子花生米,咕吱咕吱嚼着,方才把最后半句话说完,“真是闻者落泪,我见犹怜呦。” “刘润生平日里吃喝嫖赌打老婆,死了也不算亏。没想到那柳氏倒还一往情深!” 酒馆二楼,胡说凭栏而坐,望着青灰色的檐角出神。楼下堂客七嘴八舌,好不热闹,却似全然不入他耳。只是在听到一半的时候,眉梢极其轻微地动了动,露出了一瞬的疑惑。 十七看得仔细,走过来在他身边坐下,问:“怎么?你觉得这事不对劲?” “也不算……”胡说慢悠悠地开口,眼神依旧涣散着,不知定格在虚空中的什么地方,“兴许只是我多疑罢了。” “不妨说来听听?”十七一贯是懒得费脑筋的,此时却莫名来了兴趣。 “只是觉得有点奇怪。”胡说沉默了一会,还是指出了疑窦所在,“刘润生既然大醉到床边起火都不知不觉的程度,为何不一进门就呼呼大睡,反而有意识和力气爬上二楼?” “额……”十七挠了挠下巴,忽地眼睛一亮,挑眉道:“要不,咱们去现场查查?” 胡说闻声,这才缓缓收回飘散的视线,轻轻落到面前的青衣男子身上。 心思细密如他,又怎会不知道,十七破天荒地主动撺掇他查案,无非只是希望转移他的注意力,好叫他不至于为了与辛夷郡主的重逢而陷于失意之中。 胡说嘴角牵动,掠过一个浅淡的笑意,拂了拂衣襟站起身来,“好。看看也无妨。” 5 刘润生的家位于两条街外的安平坊。一栋临街的二层小楼,是刘家祖上传下来的老宅。火灾已过去大半日,呛人的浓烟味仍旧盘桓不散,斑驳的墙体被熏烤得发黑,门窗都成了无遮无挡的黑洞,显出一种岌岌可危的颓态。 府衙已判为意外事故,只是还需走些登记立卷的程序,便暂时封了现场,象征性地安排了一名衙役把守。此时,那衙役正倚着门框,百无聊赖地打呵欠。 十七塞了一点银子,两人便畅通无阻地进了门。 一楼进门为堂屋,左右各为厨房和耳房。因为火是自二楼燃起的,故而一楼的受损程度并不严重,只是救火的人进进出出,弄得十分凌乱。 胡说转了一圈回到堂屋中央,盯着脚下的地面。四面的墙壁与家具的表面都多多少少泛着焦黑,唯独地板,除了印着杂乱的脚印外,几乎没有炙烤的痕迹。 上至二楼。厢房作为起火点,损坏最为严重。残骸满地,只能连蒙带猜地还原现场的本来面貌。 床榻和小几已经被焚烧得看不出形状。十七指了指这两块一大一小的黑疙瘩,边说边模仿着做了一个挥胳膊的动作,“刘润生就是在这睡着,然后碰翻了小几上的烛台,灯油洒在了铺盖上,连同床幔一起烧了。” “呦,这还有个檀香炉。”十七脚尖一抬,从灰烬里踢出一个青铜金猊状小炉。香炉被火焰烤得锃亮,但毕竟是金石之物,倒是完好无损。 他叽叽喳喳分析了半天,却不见胡说回应,抬眼一看,胡说正站在门口,若有所思地端详着脚边一块缺胳膊少腿的物件。 “这是什么?”十七问道。 “我猜……是一把凳子。” 十七瞪着眼,左看右看,四个光秃秃的木头棍,长短不一地杵着,确实是把凳子。“凳子怎么会摆在门口?这不是添堵么?” “是啊。”胡说点点头,放眼望着满室狼藉,脸色一分分凝重,“凳子,怎么会摆在门口呢?” 6 “现场有三处疑点。” “第一,一楼地面为何相比于其他地方,受损程度最轻?” “第二,二楼门口为何会不按常理地摆置一把凳子?” “第三,明明一楼就有耳房可以休息,为何酩酊大醉的刘润生要不嫌麻烦地上楼?” 胡说边走,边向十七解释。 “所以,这场火,并非表面看起来那么简单。”十七很快领悟,“你怀疑柳氏?” 一离开刘家,胡说便马不停蹄地走访了刘润生与柳氏在案发当日去过的地方。此时,他们已先后去过刘润生常去的赌坊和当晚柳氏打酒的酒铺,正赶往下一个地点。 “可是,柳氏即便有的动机,也没有纵火的条件呀?酒铺的老板连同伙计好几人,都证实了起火时,柳氏确在酒铺无疑。” 胡说淡淡一笑,不置可否,任由十七在一边碎碎念地自问自答。两人脚下生风,不一会便到了目的地——浮生香铺。 根据柳氏的口供,她在案发当日白天,曾来此处购买檀香。回家后,却被刘润生误以为与人私会,当街发生争执,也就是那时遇上了十七出手解围。 两人甫一进门,一缕幽静的香气便如迎宾的美人一般,袅袅娜娜地缠上了鼻间。 店内三面墙壁都被高达屋顶的木格架子占据,分门别类地摆放着各类香料,杜衡、甘松、苏合、安息、檀香、乌沉香、迦南香……一应俱全,琳琅满目。矮柜上还陈列着手炉、香囊、香函等各式器具。角落里立着一台三足熏炉,铸铜鎏金錾刻,高达四尺,胎体厚重,釉色莹润,炉内燃着暗金色的幽焰,紫烟丝缕逸出,在空中飘散曼舞。 一名女子正背对着门口,在货架上归置物品,听到动静后,闻声回首,与胡说二人打了个照面。 这浮生香铺的老板,是个寡居的妇人,女子家的名讳总是不便打听,只知道大家都唤她为念娘。念娘约莫二十七八的年纪,五官秀丽,眉眼生动,虽不算妙龄,但一颦一笑,皆有种说不出的妩媚风韵。 胡说表明了来意,又揖礼道了句叨扰,念娘脾气颇好,配合地翻了翻账簿,指着其中一条记录,“没错,柳氏昨日的确来过,购浮生香二两。” “是炉子里正在点的这一种吗?”胡说看着屋角的香炉。 “正是。这是妾身自己调制的一种香料,以沉香为主料,佐以丁香、白芷、独活与高良姜,有静气安神之功效。燃此香助眠,可一梦至天明。遂斗胆化后主‘世事漫随流水,算来一梦浮生’为己用,名之‘浮生’。”念娘含笑娓娓道来。 “确实是好香。”胡说笑道,又问了些其他关于柳氏的事情,得到的回答与酒铺老板大同小异,都道是没有发觉柳氏有何异于平常之处。两人谢过念娘,辞行前,胡说还顺手购买了点浮生香回去。 “熏香不是易耗之物,每晚只需微量燃用,这二两香,可用一月有余。若觉得好,莫忘再来。”念娘一边称香包装,一边殷勤说道。 “再多要一点。”胡说看着折好的纸包,突然道。念娘依言又称了一两,他却仍嫌不够,如此加了两次,方才满意,付了钱,笑着接过包裹。 “这位爷,真是照顾妾身的生意。”念娘笑吟吟地看着胡说,将他们送至门口,躬身福了一礼,目送二人走远。 7 闻冤铺里。 “你可是有线索了——阿嚏!”胡说一回到铺子里,便将金猊香炉翻找了出来。作为“神棍”套装之一,这香炉久未使用,一掀开盖子,灰尘四扬。十七跟在他后面,正在张嘴追问,好巧不巧地吞了一嘴巴的陈年老灰,差点没背过气去。 胡说慢条斯理地清理着香炉,“算是吧。” “咳咳……”十七好容易吐完了嘴里的灰烬,皱着脸,“不是,我说你捣鼓这玩意儿干啥?” “你看看这包香,体积大小与那日街上柳氏掉落的那包,是否接近?”胡说没理会他,反而提起方才买的香包,戳到了他的鼻子跟前。 “唔,差不多吧。”十七回忆了一下,“似乎比柳氏那包还要少些。” 胡说点点头,打开了纸包,将里头的盘香悉数放进了香炉中。 十七围着忙碌的胡说打转,“哎,你说咱们接下来干吗?” “接下来——”胡说已经点燃了浮生香,终于抬起眼,好整以暇地看着十七,认真地吐出了两个大字,“睡觉。” “……” 十七眼睁睁地看着他扯了一个蒲团枕在颈后,舒舒服服地和衣而卧,没过一会,声息渐低,呼吸浅长,竟就自顾自地睡着了。 这又是哪一出嘛! 十七一头雾水,几乎把后脑勺挠成了鸡窝。 浮生香静静燃烧。许是胡说点得太多,香味过分厚重了些,十七有些不适,看了看酣睡的胡说,只好无奈地退出去,回手掩上门,去隔壁自家的酒馆里顺了一壶酒,随意地倚坐在台阶上,慢慢喝着。青衫落拓,眉间凝着不易觉察的戒备。 人来人往,看见他,都会招呼一声“十七老板”。谁也不知道他姓甚名谁,来自哪里,为何会有一副深不可测的好身手。这座酒馆和毗邻的闻冤铺一样,似乎都是一夜之间,凭空蹿出了头,就此在棋盘街上驻扎下来。 和胡说在一起的时候,十七近墨者黑,也被传染成了半个话痨。然而一旦自处,青衫男子却仍是如旧日一般,沉默寡言,冷眼看着帝都的锦绣繁华,眼底若隐若现地浮着刀刃一般的光亮。似乎除了那个神神叨叨的算命先生,外人外物都与他毫无干系。 十七就这么一边饮酒,一边不声不响地思忖着什么。一壶酒将将喝完,闻冤铺内骤然响起了惊呼! |
转载请注明地址:http://www.hulubaa.com/hlbzz/11270.html
- 上一篇文章: 4本锻炼身体就变强的小说,主角铁血真汉子
- 下一篇文章: 没有了